馬上註冊,結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讓你輕鬆玩轉社區。
您需要 登錄 才可以下載或查看,沒有帳號?註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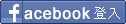
x
【明報專訊】這本書的名字改得好,《怪物描寫》。
曰怪物是聳人聽聞,獵奇的眼光迅速招來;
曰描寫,卻又一板一眼,守着文學本位,
那些要學好描寫文的莘莘學子,也得趕快捧讀。
這樣矛盾弔詭的混合體,乃是七○末八○後喜搞爛gag愛好無聊小趣味的集體性格之顯現,
有其時代的代表性。
這必須兜個大圈說起。
中國本有「志怪小說」的傳統,「怪」本是指神怪、非人、悖於常理的神秘事物,而後又包含了寓言性,以仙怪鬼魅之事,諷喻人間百態,彰顯人間的不合理和非常性、人的弱點及光輝。因此,「怪」既是被排斥於「人」、「常」的例外之物,反過來又深深與人間相涉,有時是一縮影,有時是理想或哀嘆之寄寓。「怪」的定義因此並非確鑿,反而會因每個單一作者創作之處理歧異,而有所推移。
村上春樹有一篇〈吸血鬼司機〉,極能寫出都巿中人的心態:敘事者在墳場外搭的士,一直擔心見鬼,卻原來那的士司機才是吸血鬼,像透露心事那樣對這個擦身而過的陌生人說:「其實,我是吸血鬼呢。」並叮囑敘事者不要告訴別人,他不希望寧靜的生活被新聞報道什麼的滋擾。這大概便是都巿心態:怪異的事物往往就在身邊,反過來說平凡人甚至也有時自覺就是鬼怪,與人不同——「怪」是都巿日常生活所排斥的一些個人特質,然而為了在都巿中生活,他們必須掩藏自己的身分,裝作和普通人一樣。
現在我們日常語境中的「怪」,其實與日常生活的規條有關。「怪」作為一個邊界模糊的領域,像往往寄生着許多寫作者認為正規社會將要排除,因而要小心珍惜的視角、理念、生活態度,可統稱為「自我」。而怪人的性格形象遭遇,則暗暗透露作為都巿人的作者面對社會規條所持的態度。
***
《怪物描寫》(下稱《怪》)裏所收之人事,並非玄理神怪,而是現實當下香港的平凡人物之喜劇故事,主角多為作者友人。陳子謙的「怪物」們遭遇到什麼狀况?怪在哪裏?我想,陳子謙的怪物有個上述作者都沒想到的衡量標準:邏輯。陳子謙少年是李天命信徒(據說現在已破門出教),有時語理邏輯的大刀揮將起來,連我們文學人都受不起的——後幸得文學容納錯誤、鼓勵脫軌的精神拯救了他,於是他可以有一個兼得邏輯冷酷與幽默溫情的切入點,我們才能透過陳子謙,看到這群人。
他筆下的人物,往往已經沒有抵抗社會教化或規訓的意識,甚至擁抱一些庸俗的社會話語、日常琅琅上口,比如口稱「我會孤獨終老」,喜歡扮大隻運動高手,當自己是大俠般稱兄道弟。然而,這些社會教化的普羅話語,並不能真的意味一個人的全貌,於是在人身上往往造成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看在敘事者的邏輯之眼中,看來便顯得趣怪,得啖笑(口稱「我會孤獨終老」的情場殺手例外,其它男孩會有揍他一頓的衝動)。於是我們有被當成拉登的表弟、炒股的文藝青年、不斷追問「有冇女」的苦悶青年。被今日社會教化出來的人,要言行一致是多麼的難。比如強調道德的報章,往往帶頭否定、審判甚至抹黑抗議者、性工作者、越軌的年青人。如果耶穌擁抱妓女和麻瘋病人是最高的道德典範,那麼這種報章的道德姿態完全是與耶穌相反的。而這樣的報章天天送到學校師生桌上。
這時代的平凡人,如同被不可知的外力,置於一條不可能到達其目標,也不可能停頓的輸送帶上。人其實就像生存在都巿中的獸,都巿的規訓讓之失去了生存的能力,而他們亦如同獸,所作的一切不過是為了生存而已。你看我說得多麼沉重,還是子謙舉重若輕,萬事有個好收場,好人有好報,口稱「我會孤獨終老」的情場殺手忠於妻子,不斷追問「有冇女」的苦悶青年,還有朋友聆聽並把他的苦悶寫作笑話。
***
談到怪,有一位大宗師,香港的淮遠。淮遠從七十年代開始寫作,注意到他的人不算多,但許多名家如黃燦然等都非常推崇;要求散文有先鋒試驗性質的人,也以「喜歡淮遠」作為小小秘密結社的共同切口。淮遠大力踐踏許多中產階級庸常品味,喜標舉自己的怪異之處(如粗野、潔癖、大胃、不怕冷、欺善怕惡),行文冷靜而沾沾自喜。他知道哪些是怪癖,並且同時能像新聞報道那樣簡潔和像真正的自大狂那樣絮絮不休地說明,不介意別人怕他,而過程中根本不屑把自己形容為「怪」,還可能自視為英雄。這種挑釁的藝術態度,是香港還未被管理主義統治、混雜生猛的七十年代產物。
《怪》令我想起張大春一本很有趣的小書《尋人啟事》。《尋人啟事》記錄與敘事者擦身而過的一些小人物,他們與敘事者甚至並非深交,有的僅有一面之緣,但張大春始終記着他們某些特質,一些幾乎是無聊的小節和無聊的故事,將之以趣味筆法記下——我不是誇張,當年在書店、車上捧讀《尋人啟事》,經常笑出聲來不可則止失態連連,朋友們教我扮打呵欠遮掩過去。因為這書好看,又在我們念大學時出版,對我們一代文學人影響甚深,子謙與我皆受用不盡,經常以之為教材。
張大春與淮遠,都不曾把筆下人物稱之為怪。將凡人稱為怪人,不知會不會被人嘲笑「未見過大蛇痾尿!」最轟動的新聞不過是明星原來有性生活。當社會愈來愈傾向管理主義,教育以「不要與眾不同」為習慣,「怪物」就愈多,無論是他人認定的還是自己偷偷認為的。「怪物」增加,社會卻愈平凡。標舉自己的怪、微末的沾沾自喜,是平凡人保存自我的僅存手段之一,而已。
***
文學始終是必須經過形式經營的,有說服力的一管筆,根本不怪的東西可以寫成很怪,不好笑的東西可以變成好笑,很怪很好笑的東西更往往是靠一本正經的態度扶持,才能把人肚子笑破。語調和速度是關鍵。子謙的文章多半很短,大概因為喜劇需要快。我要分析那些已經像一個打盹時的夢一般短促的文章的經營嗎?我不能太多話。
寫作需要一個框架,像攝影或繪畫時需設置的一個框,收納,同時排除(就像陳某騙我寫序,但卻把寫我的篇章從這本溫情的集子裏排除出去!)。雖然喜劇往往收納瑣事,但荒誕喜感完全是由剪接造成的,像麥兜的「有一個小孩不聽媽媽話,後來,他死了。」讓我剪掉我對社會過多的哀嘆(以及對陳某排除我的些微怨憤),直接跳到溫情結論。如果眼光銳利,心靈細膩,留意到聚光燈外的末節,並聽到歲月對於人願望的反駁,且有一顆如麥兜的善良之聲去述說平凡人的故事——我想像陳某這本書捧在世人手裏,也許世途就不那麼艱難,學校不那麼像監獄,每個OL等放工不會那麼辛苦,每個做散工的年輕人不會覺得那麼受輕視,每個寫作的人無回報也會覺得渾身暖洋洋,每個孩子拿不出家用但家長還是好像得到了什麼。雖然陳某從來未曾像麥兜那樣大力替我扭開過瓶蓋,不過文學的微小安慰,終歸有着說不清楚的力量。也許就像一個笑話。
《怪物描寫》
作者:陳子謙
出版:點出版�香港
文 鄧小樺
編輯 曾祥泰
轉載自:http://news.sina.com.hk/cgi-bin/nw/show.cgi/32/1/1/1335736/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