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註冊,結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讓你輕鬆玩轉社區。
您需要 登錄 才可以下載或查看,沒有帳號?註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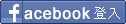
x
應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四海為家的秘魯小說家略薩(Mario Vargas Llosa)著作等身,至今創作了十六本長篇小說,六十至七十年代有五本,八十至九十年代有七本,新千禧年至今有四本,還寫了大量戲劇、文論和政論,他主要的身份當然是小說家,也曾夫子自道,認為「說故事的方法」與「作品的結構」對他的小說創作來說是同樣重要的。「結構寫實」是略薩小說的獨門秘笈,其中一種獨創心法就是「平行敘述」--兩年前,他在「略薩作品研討會」上說,他的創作可歸納為兩個關鍵詞:其一是「說故事的方法」,即如何將故事說好,其二是「作品的結構」,即如何讓寫作方式成為作品的主角。在他看來,兩者同樣重要。
命運共同體:《對倒》與《巴別塔》
所謂「平行敘述」,就像電影的蒙太奇,或畢卡索(Pablo Picasso)的立體主義繪畫,將表面上互不相干的人物或情狀並置,達致作品結構立體化的藝術效果,比如《三國演義》,說來也是一個類近的平行敘述結構。劉以鬯的《對倒》正是一個上佳的例子,這篇創作於七十年代的小說講述的是一個城市的社會現狀與歷史背景交織的故事--那是來自內地的中年男子淳于白與土生土長的少女亞杏這兩個表面上毫不相關的人物在同一社會(香港)與同一場景(旺角)的「平行敘述」。
另一個「平行敘述」的顯例是墨西哥導演艾力謝路.依拿力圖(Alejandro Gonzalez Inarritu)的電影《巴別塔》(Babel),劇情由一顆子彈跳接並連貫了一些摩洛哥人、美國人、墨西哥人與日本人錯綜複雜的人生際遇,此君的前作如《狗男女的愛》(Amores perros)與《21克》(21 Grams)等均擅於以多線「平行敘述」,展陳表面上互不相干的人物或情狀,最終總是在互相鑑照的過程中,隱隱然浮現出一個教人思之惘然的「命運共同體」。
略薩早期的小說主要書寫秘魯在軍事獨裁統治下的社會百態,比如《城市與狗》(The City and the Dogs)力陳五十年代軍事獨裁統治的殘暴與腐敗,秘魯社會形同一座巨大的監獄,《綠房子》(The Green House)的背景是沙漠城市的一間妓院,當中的眾生悲歡與亞馬遜河流域的冒險事業的興衰互為對照。他其後的作品總是將歷史素材融入小說,那就是說,靈感源自廣泛的閱讀。
《世界末日之戰》(The War of the End of the World)所寫的是巴西農民起義,略薩在「獻詞」中寫道:「謹將此書獻給另一個世界的達.庫尼亞」。達.庫尼亞(Euclides da Cunha,1866-1909)被譽為巴西最偉大的作家,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是《腹地》(Rebellion in the Backlands),《世界末日之戰》正是從《腹地》這部「巴西民族主義的聖經」取材,以全新的寫法和結構為經典賦與新的意義,並且以重寫經典的實踐過程,示範了如何將寫作方式和結構方法變成一部作品的主角。
《天堂在另外那個街角》(The Way to Paradise)的靈感也是源自一本書,略薩說:「我閱讀了科娜.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1803-1844)的《一個賤民的漫遊》(Peregrinations of a Pariah)。她對獨立不久的年輕共和國的描述打動了我,她還談及到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講出了非常隱秘和敏感的事情,也打動了我。」
科娜.特里斯坦的父親是秘魯人,母親是法國人,她長期參與社會抗爭,而她也是畫家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的外祖母,儘管孫兒高庚在外祖母去世後四年才出生,略薩卻施展了他的單門秘笈,採用平行敘述結構,單數的章節講述外祖母特里斯坦的抗爭故事,雙數的章節則講述孫兒高更遠赴大溪地追尋精神淨土的故事,並且以這樣的平行結構指向精神抗爭的核心隱喻:精神上的天堂就在街頭不遠處。
「在地的中國人」與「不在地的秘魯人」
過去一個星期無疑是震撼人心的「諾貝爾周」,陸續公布的各個獎項得主各有各的故事,文學獎得主略薩長期四海為家,1990年競選秘魯總統落敗,在二十年後的今天看來,真的不知道是他人生之大幸還是不幸;劉曉波並不是唯一為中國民主、人權而有所犧牲的國人--正如為南非、緬甸的民主和人權而有所犧牲的人不可勝數,但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與昂山素姬(Aung San Suu Kyi)最可貴之處,無疑是用上了一生最寶貴的時間在非自由的國土的牢獄中與獨裁統治長期鬥爭,甚或可以說得誇張一點,對這些在不同的獨裁統治的國度裡被長期囚禁的公共知識分子而言,再沒有什麼比「在地」抗爭更有意義。
長期四海為家的略薩當然也反對獨裁統治,他二十四歲便在巴黎完成了第一本長篇小說《城市與狗》因深刻揭露秘魯軍政府的腐敗與暴行而被「焚書」;劉曉波因言論觸及當權者的痛處而長期被打壓、軟禁乃至陷獄,但仔細分析,他所說的和他所做的其實不過是一個開放社會最起碼的常識,他寫給妻子劉霞的情書只附錄於一封向世界表白心跡的公開信中,他說:「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那真是一首與高壓統治的殘酷時代平行敘述的詩,可他對失去最基本的人權和自由無怨無悔,並且向全世界宣稱「我沒有敵人」,更胸襟廣濶地讚揚看守所主管劉崢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
略薩與劉曉波兩人在一周內先後獲頒諾獎,說來約略也是一種文學與人權的「平行敘述」吧,一個「在地」,一個不,可也殊途同歸,此刻便想,如果借用這種「平行敘述」的手法,大概也可以寫出「不在地的秘魯人」略蕯,與乎「在地的中國人」劉曉波的動人故事吧。
免於「和音化」與「裝飾音化」
劉曉波一如曼德拉和昂山素姬,一旦流亡國外,可能是另一個故事了,因為他們一旦不再「在地」,到了西方,便會成為無數的西方自由呼聲的其中一些「和音」,成為某些人人都奉為生活常識的普世價值的「裝飾音」(ornaments),無法再凸顯自身的意義了。如此說來不免是一個無比殘酷的悖論--「在地」囚禁的種種犧牲如果就是自身存在唯一的意義,那意義無疑是絕對的不公義,可是沒法子,他們幸或不幸,正好活在一個公義長期缺席的世界。
也許「在地的中國人」劉曉波與「不在地的中國人」魏京生剛好構成了另一個堪可「平行敘述」的故事。我們這一代人對魏京生都很尊重,據我所知,七、八十年代為魏京生而寫的詩和文章,真是車載斗量,只是魏京生並不明白,以一生最寳貴的時光「在地」抗爭是一個無比殘酷的悖論,因此才會公開表示,有不少人「比劉曉波更有資格獲諾貝爾和平獎」,這樣的話未免太酸了,酸得令曾經很尊重他的人都不免有點傷心。
魏京生也曾因言論陷獄,也曾受過非我輩所能體會的苦,我們這一代人真的很尊重魏京生,可是在聽到他可以流亡西方之後,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他終於重獲自由了,憂的是他曾經震耳欲聾的聲音會被「和音化」及「裝飾音化」,甚或逐漸「自我滅音」。魏京生大概不明白,諾貝爾和平獎有時不免是個國際大笑話,他也不明白這個獎並不是一項要分出高下的比賽,尤其並不是一項比拼誰受苦更多的比賽。
劉曉波的文章也許寫得並不特別好,比如他討論八、九十年代以降的色情文化就多少都有點頭巾氣,又比如他撰文探討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7-1274)的政治思想,寫得略欠神采,還有點沉悶,然而,他在《我沒有敵人》這篇短文卻出奇地氣定神閒,出奇地虛懷若谷,那是一種大悟而豁然之境,絕對不是魏京生所抨擊的「對政府有更多合作的表態」、向中共政府投降或向溫和派示好。
劉曉波說他對檢察官、警察和看守所主管都能感到「尊重和誠意」,正是基於以下一段擲地有聲的思考過程:「……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毁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劉曉波與魏京生的故事還會「平行敘述」下去,誰都不知道這個「超級長篇」會出見怎樣的結局,但不用急,曼德拉在獄中的時候,其實也不可能知道南非往後會主教圖圖(Desmond Tutu)和他自己獲頒諾貝爾和平獎,還有作家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庫切(J. M .Coetzee)獲頒諾貝爾文學獎,但他心中肯定有一個信念,很多年後才得以實現,得以成為一種免於種族歧視與種誤隔離的新國家的藍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