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註冊,結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讓你輕鬆玩轉社區。
您需要 登錄 才可以下載或查看,沒有帳號?註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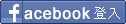
x
《東西》之辯——讀梁秉鈞(也斯)詩集《東西》
江濤
——《東西》是什麼「東西」?「東西」是什麼意思?
——《東西》是詩人梁秉鈞的一本詩集;《東西》是一本在原版本(香港•牛津出版社)的基礎上,同時收錄了《游離的詩》、《蔬菜的政治》部分詩作,並將以原名在廣州出版,籍此向國內詩人推介的詩集。這本新編的《東西》分七輯:「東西」、「東西牆」、「東西行(之一)」、「東西行(之二)」、「新邊界」、「東西書簡」、「《詩經》練習」。至於「東西」是什麼意思?接下來,就是本文所要闡述的。
一.「東西」:[thing];[people and animal]
[thing]——泛指各种具体或抽象的事物;
[people and animal]——特指人或动物(常含喜爱或厌恶的情感)。
在詩集《東西》裏,不乏這樣的「詠物」或「詠人」的詩篇。如《東西》第一輯「東西」裏的詩歌:
<蓮霧>——……我認識你不自今季/一再回來尋覓踪跡/寒冷的日子等你結果/從暗澹等到明亮/知道你變化的顏色/並沒有向你要求新奇/只望你繼續是你自己
<黃色的辣椒>——……從糾纏不清的植物關係裏/展開自己以爽脆的笑容/黃色的辣椒/紅色的辣椒/我會永遠支持你/對抗平庸的口味
<帶一枚苦瓜旅行>——……咀嚼清涼的瓜肉/總有那麼多不如意的事情/人間總有它的缺憾/苦瓜明白的
<菜干>——……你說瘀青的身體裏/真的曾有矯健的身體?/阿婆讓我再喝你煮的湯/試嚐裏面可有日子的金黃
再如第三輯「東西行(之一)」裏的詩歌:
<錢納利繪畫濠江漁女>——……天足輕快走過的堤岸,他敢走出去嗎?/哪兒將有充滿匕首與黑煙的危險戰爭/他害怕可又不甘心在圍牆內取暖與慨嘆/仍想要走遍大街小巷,要忘記/自己的出身,重新活一次別人的生命/從那爽脆的笑聲和海風溫柔的胸懷裏/從頭繪畫出自己的身世和歸宿
<鄭觀應在大屋寫作<盛世危言>>——……高曠的大屋一天一天變得殘蔽了/地產商和有司的爭執沒有解決問題/歷史只是一堆破磚爛瓦嗎?/高牆外綠蔭中好似掩映舊日樓瓦簷角/撥開野草和蜘蛛網/步入空寂無人的別院
<一頭從埃及長途跋涉去到巴黎的長頸鹿>——……只是你沒法把我包紮/也不能把我塞在艙底/因為我是一頭長頸鹿……我留在植物公園踱步/總有孩子老人來看我/瘋子和藝術家記得我/不因為我有什麼功績/只因我是一頭長頸鹿
中國傳統的古典詩有一種文體是「詠物詩」,像古人詠蓮詠竹,借以寄寓人格的理想,或道德的批判。梁秉鈞在《東西》 後記中,對此亦有論述:
——「我的詠物詩不一定是借喻,對不同事物的物質性也感興趣,不想僅以一個既定觀念投射到諸物身上。」;
——「我書寫球鞋、苦瓜或是辣泡菜,尤其對我們與當代諸物的複雜關係感到興趣」 ;
——(例如)《食事地域誌》裏寫香港新界圍村節日的<盆菜>,這種層層混雜各種肉與菜的食物,也啟發了我用一種拼湊各種不同聲音和觀點的手法,以表達我們對九七的複雜心情……;
——在《食事地域誌》場刊的封底,有一張李家昇和我的照片,仿似當時中英雙方在和談桌上談判,我們各據餐桌的一方,卻是朋友談笑商量;不是為了決定他人的命運,是為了善待吃進口中的食物,細味它們不同的特色……我們都想從城市到城市,繼續我們對食物和城市文化的研究。
以上,「東西」是一種「物像」——事物(食物)、人物、動物,它是「物本身」,同時隱含著一種「人與物之間的關係與態度」——於此,「東西」表達的,是一種書寫的立場、界線、溝通與交流。
二.「東西」: [east and west];[four directions of north,south,west and east]
[east and west]——东面(邊)和西面(邊);
[four directions of north,south,west and east]——泛指四方八面。也特指周邊。
邏輯上,當我們強調地理方位的不同於相對,潛話語即是:分離與隔閡;當強調外圍與周邊,其潛話語即是:邊界與關係。
在詩集《東西》裏,第二輯「東西牆」以曾被「一牆之隔」的「東西歐」、「東西柏林」 為詩寫題材,重在寫「分離與隔閡」。在《游離的詩》後記《書寫游離》中,詩人曾提及這段創作過程:「……尤其看到圍牆倒塌,東歐變天,更令人在期待之餘,亦復又不少感慨。我九O年才到柏林,在東西德幣制統一之際在那兒住了一個夏天,乘著地鐵,不覺就踏上東邊的土地,看見新的氣象,但同時也看見隨來的新的問題。」如下詩歌所寫道:
<牆的故事>——牆倒下了/我們看得更清楚嗎?……我們帶著我們的牆走過牆
<奧斯維茲集中營舊址>——……應該有點燃的燭光/給亡靈予安慰?/應該有一雙更大的手/承載著委曲的殘骸/喻示經過災劫/會找到新生的意義?/我只看見空洞的鏡片/瞪視著一個無影的空間
<雨後的歐洲>——……外面雨下個沒停。在動物骨骼砌成的廢墟裏,在傷疤累累的地圖上,在半拆和新建的牆中間,在海藻纏綿蕪雜的潛意識中相遇,我參觀了一場又一場因歧見而生的炮火,由偏見而來的屠殺。
而第五輯「新邊界」則以被「國境」割分成關係複雜的社會政治經濟形態的香港與鄰近的珠三角、澳門地區的關係。在《東西》後記《食物•城市•文化》中,詩人寫道:「今天不僅是我自己生活多年的城市發生了種種奇怪的變化,我們重視的素質變得愈來愈不為大多數人重視。在鄰近的特區或沿海城市裏,由於封閉而至門戶大開的過程帶來種種畸形現象。西方的資本主義與東方的政治現實有了最荒謬的結合……」:
<鄰葉>——……把我們釘在植蓮的版圖上,繪限我們的身份/黑暗的傷戮並非我們的追求,艷紅的花朵/豈只是俗色霓虹?個人意欲舒長寬大的葉子/超越歷史晃盪的池水?……帶著各自殘缺的歷史,我們會長出怎樣的新蕊?
<后海灣>——……海水沒有邊界/飛來遠方的禽鳥/也飄來另一個新建城市的泥塵/飄來另一條河的浮粕/建築的羣落沿水生長/地樁插入泥土生根/工廠的污染流金河裏/公路上傾倒的廢料沿河入海/一陣陣灰黃的煙霧/緩緩向這塊土地淹過來
<媽祖廟前>——……面對起伏的灰色波濤飲酒/酒罐上有慶回歸的的金字/今天天氣陰晴未定/黃昏來時有點翳熱……
的確,生活教諭我們的常識(真理)是:在有分界、界線、界限存在的同時,必然有溝通、交流和打破界限的存在!而交流與交往,也會帶給我們新領悟、思想的新眼界、新領域!
三.「東西」: [from east to west]
[from east to west]——指的是「東與西」的一種距離,也是「東與西」交往的一種過程。
在讀詩人在《東西》後記時,我讀到的,更多是他在自己寫作中對「東與西」某些微妙的思辨:
——我從對食物的興趣開始,逐漸沉迷在這些跨越文化的歷史人物傳奇中,僅僅是「東方學(Orientalism)」式的文化批判好像還說不盡其中的嚮往與慾望、那種充滿了誤解與了解的求索。是什麼令一個人想離開自己的文化去擁抱另一種文化,一個人在另一類文化裏看見什麼,盡心探求帶來多少的痛切與狂喜?
——我逐漸發覺不是有一個西方與東方,而是有許許多多相互混雜產生的東西。若我在西方對人情和食物充滿懷念,亦好似因距離而時時連起看見了經濟與政治。
——我喜歡生活在不同城市,接觸不同文化,但又同時知道跨越文化是不容易的。我既遇見種種不同的東西,又是帶著它們跨越邊界,有時倒是它們帶我跨越了我自己認識的邊界。物質現世的屬性令我免於抽空的崇高。東西古怪的樣貌挑戰了我原有的觀念。
——我們今天很難再只是簡化地說西方打量東方、用陳腔濫調把對方歪曲定型;東方同樣也在用既定的目光端詳西方,用自己的偏見為對方照像呢!我們只能在種種偏執的夾縫裏,感到荒謬之餘也試找一些空間,試去發現其他種種可能的看法與關係。
詩集《東西》的第三、四輯被命名為「東西行」,題材涉及東西歐、東西柏林、東西方、港澳與中國大陸周邊地區在歷史與文化上的種種誤解與交融……其主題皆指向這種「因距離與隔閡產生的交往過程」:
<柏林的地址>——我們分享了共同的地址/不同時間同棲於異國的園圃/到頭來終於結出不同的花果/我們如何闡釋悲劇?……在邊緣我看到失去故事的女子/死去了再死去一次/當神話的傳播與建構/參與經營殘酷,矯情與謊言強把個人回歸了/種種家園,漂泊的異葉需要更堅毅去抗拒/歧異被收編,變成可接受的一葉浪漫傳奇
<誰要是輕易遺忘,敢情是可憐蟲!>——……我好似知道了事物隱秘的聯繫/當我沿著河/來到這冬天的早晨/從圍繞的棚架和帳篷背後/認識了你的塔尖,知道你/還是想像你?……
<重畫地圖>——……我們在心裏不斷重畫已有的地圖/移換不同的中心與邊緣/拆去舊界/自由遷徙來往/建立本來沒有的關連/廣漠中偶然閃過/一些游離的訊息/在浮泛的光幕底下/逐漸晃現了陸地的影子
四.「東西」:產生關係、衝突與達成新和解的地方
正因著距離與界限,產生了物與人,地理上的東與西的關係。故「東西」不僅是人之界、物之界、距離之界、時間之界、觀念之界、文化之界、語言之界、情感之界……本身,同時亦是其關係和潛在的可交流規則。
詩人葉輝在《<東西>若干種讀法》中,就從「從物質到人性」、「從『異』到文化身份 」、「從幻由人生到抒情境界」、「物的秩序及其疑點」這幾個涉及距離與游移的事物關係與語言過程去論述的。另,詩人陳智德的《遷徙、移民與放逐——梁秉鈞<東西>選讀 》也有類似的觀點:「《東西》所涉及的內容正涵蓋了經驗上和觀念上的遷徙、移民與放逐,並多角度的、正視現實限制的態度來看新與舊、東和西。詩的非精確性所表現的含蓄和多義衍生的可能,正有利於表達這種複雜而多面的、難以概括的想法。」
如果說,在詩集《游離的詩》(1995),梁秉鈞寫的是遷徙和漂泊,現實上和心理上的游離,在詩集《東西》(2000),詩人在經歷了多年的漫遊(地理或心理)後,他說:「我在《東西》這本詩集裏從東方寫到西方的旅程,發覺並不是只有一個東方和一個西方,而是從中互相滲染互相矛盾產生許許多多的『東西』……」,而在對這些如同現象學大彙聚的「東與西」的思辨與詩寫後,在詩集《蔬菜的政治》(2006)裏,透過對世界各地食物為主要題材的寫作,同樣的主題,詩人呈現出更廣闊深厚的包容態度,更明確的文化和語言立場:「我的詩無可避免地總有我的意見及批評,但我希望這是出於對自己的反省多於去貶低別人……選擇怎樣的食物,變成選擇怎樣的生活,選擇我們變成怎樣的人。不光是口味,也是健康倫理價值觀甚至政治了。我們常常以為自己是自由的人,可以選擇一切,其實我們未必完全可以自由選擇放進口中的食物,有時是由於政治的禁忌商業的霸權,有時源於我們自小受他人影響形成的歧視和偏執……食物既連起社會與文化,又連起私人的慾望與記憶,有不少豐富的層次。作為一個寫作的人,當然想細嚐生命中各種滋味,令我們體會不同深淺的情意,見識生活的幅度,感激他人創造的甘美,旁觀眾生的酸苦哀矜勿喜。」(《蔬菜的政治》•附錄《羅貴祥、梁秉鈞對談》) 因此,或許我們也可以這樣去理解,從《游離的詩》到《東西》到《蔬菜的政治》,恰是記錄了詩人梁秉鈞對其一直關注的「東西」(題材/主題/寫作風格)的思考和詩寫過程——因此,「東西」也慢慢呈現了它的具體或抽象(包括語言)的本真:產生關係、衝突與,達成新和解的地方。
如《東西》的第六輯「東西書簡」:
<有關翻譯的通信>——……各自經過了悠長的逆境,拒絕/輕易的字眼敘說身心的感變/在沒有解釋的地方,嘗試去體會/另一個人沒有說出來的那句話/獨自放棄累積的部分,更換/自己,面對零再重新開始/一個新的生命,永遠連接著另一個/孤獨的人,原來在沉默中想的話/保留前面未說完的,引向後來/不是結果,還有推論的過程/謝謝你與我一同走過這些彎彎曲曲的路/無言的彼此商量走出彎彎曲曲的句子
<耶魯感遇>——……怎樣把一顆島上的紅豆/翻譯成白亮的珍珠/又怎樣把異國校園兩排樹木/翻譯成一對中國對聯?/我們是不斷翻過來翻過去的/輪轉的花草,遞增的名字……
<為葉輝的食經寫序>——……想像一個最悲壯的進食所在?/想像一場最纏綿的進食過程?/也許到頭來不過是尋找一個懂的人/不會把春韭做老……避開庸手自煮滿桌的新味/細嚼散文的廚藝與詩的火候/讓我從旁幫忙細切蔥蒜/帶出你調理的真味?
五.「東西」:發現「自我」與「他者」的語言線索
幾年前,在一次詩歌朗誦會上,聽梁秉鈞讀出他的詩歌《帶一枚苦瓜旅行》,當時沒有看文稿,只聽聲音,卻也被其中的語調深深感動,後來,更多地閱讀了他的詩文後,我回想一個問題:當時,自己為什麼會突然被那首詩打動?我聽到的是聲音,可打動我的是語調。什麼是詩歌的語調?
語言具有的聲音色彩叫語調;語氣的聲音形式叫語調;人們說話時,很少有不摻雜著情緒的,句子裏聲音的高低、快慢、輕重的變化叫語調;……通過閱讀,我發現,梁秉鈞的詩歌,從他最早的詩集《雷聲與蟬鳴》開始至最近期詩集《蔬菜的政治》,都有著其一貫的語調,就是「對話」。
在一篇與鄧小樺的訪談(「鄧小樺•與梁秉鈞的一次散漫訪談」)中,梁秉鈞戲稱自己是「對話王」,他解釋道:「……(當時,詩集《雷聲與蟬鳴》)想在主流之外,探索另外一些價值,建立一個比較親密的小社群(community),所以很多詩都是嘗試address(指向)某個人,像對話或書信那樣,有一個言說的對象。」;另外,他在該文中也說到:「可能這種聲音不太政治性,不浪漫、不宣揚,但也可以是一種聲音吧。有些人以參與社會運動來表達自己的想法,我也有參加「法定中文」的示威。但反映時代不必是「時代三部曲」的寫法,當時的想法是如何運用語言去回應時代與社會。因為對民歌、protest song有興趣,也嘗試在詩中結合口語、歌謠體,於是寫了…… 」; 在詩集《蔬菜的政治》附錄「羅貴祥、梁秉鈞對談」中,梁秉鈞說道:「我想要描述那未被描述的感情、未經細嚐的滋味、未受到注意的想法。我想環繞着那生命的謎團,逼近它發聲,展開對話。」
在一種「對話」的語調下, 這些詩寫「東西」的詩,無論在論述地理、氣候、歷史、人情、風俗、風情、私人記憶、男女愛慾、種族性別、現代生活等描述中,似都產生了一種情感交纏的「訴說」。而正是這種把讀者對象化的「對話」與「訴說」的詩歌語調,加上日常語言和口語的運用,在情緒、聲音色彩的渲染下,產生了一種親切平易的語感,迅速拉近了讀者的心理距離。「對話」使對事物的探尋跨越了地理與心理的邊界,而進入了沒有邊界的人的內心的時間之旅。
於是,在詩集《東西》的第七輯,出現了一種「新東西」,一種詩人近期的新的寫作嘗試「《詩經》練習」——對此,我的理解是,詩人正在嘗試與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的各篇章的場景進行互文與寫作的「新對話」——這或許是詩人試圖運用詩歌語言與中國古老的文化對話,亦或許是詩人所說的「環繞那生命的謎團」、「逼近那聲音的呼喚」 ……與那些在新的思想及情感領域所領悟、發現的「新東西」的「展開對話」。「《詩經》練習」不是「舊瓶裝新酒」,更是詩人在逼切的現實中,必然找到的「魔幻瓶」—— 一種籍此理解和表達個體「存在」 的「詩寫變形」。
在《七月》這首詩中,詩人嘗試以語言穿越「時間之牆」, 把《詩經•七月》的「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的回環不息的古老民謠語調,改寫成了一個戲劇化的場景,寄寓了個人命運、語言命運的發現與探索。這是詩人新近的一種寫作方向,一種尋找新的創作可能性的努力——因此,「東西」亦是發現「自我」與「他者」的語言線索。「他者」,可以是拉康意義上的與「自我」互為對象的存在的構成,當然也可以是相對與「現狀」、「目前」的「時間」與「未來」。
……
一月的山頭戴了雪的帽子
高羅岱補好了屋頂的疵漏
高羅岱有一床暖和的被窩
二月裡高羅岱從摩洛哥帶回來
掛氈和彩燈
自己造了燈罩
三月弄好了管用的浴室
四月裡田裡的菜長出小花
五月裡蚱蜢在綠葉間跳躍
蟬在枝頭起勁地叫
高羅岱修好了結他的弦線
彈起彼德西嘉和活地居菲
七月裡高羅岱参與了
村中的節慶
七月裡高羅岱用他的老結他
彈出許多老歌
七月裡高羅岱用他的老結他
彈出許多老歌
在《七月》的結尾三句,「七月……」已變成了同調回環不息的語調,如歌,如訴……哀而不傷,如同時間的季節輪迴,歷史場景的「當年今日」……這就是詩,這是形式,也是內容——這如何不「政治」了?!如何不「文化」了?!
在此文來到結語陳詞之處,再例舉一首「《詩經》練習」裏的詩《對岸》:
水鳥關關地叫
在河岸的那一邊
窈窕的姑娘
是我們早晨的思量
長長短短的荇菜
左左右右總撈不到
她來自不同的階層
她相信不同的偶像
長長的夜裡時睡時醒
反來覆去總不到黎明
她閱讀的是不同的文字
她喜愛的是不同的圖像
長長短短的荇菜
左左右右總撈不到
她相信的是另一種價值
她追求的是另外一種人生
這麽美好的姑娘
彈着琴瑟想跟她交朋友
她喜歡的是另一種音樂
她沉迷於另外一種節奏
我相信《對岸》的文思,是起源於《詩經》的《關雎•周南》,詩人沒有沿用《關雎》而用了《對岸》作題目,此意正是「詩眼」(或主旨)——從強調「對象」到強調「與對象的距離」——寓意地理、時間、心理之「界」,之「東與西」。
如前所述,距離,並不單純表現分隔與不可能,寫作,也可以是一種「越界」。在《對岸》,「她」,或象徵人類社會的未來,文化的未來,語言的未來,一切美好願望的未來,當然,也可以是詩人的「託物言志」的「自我對象化」幻影,或單純到指向某個體的人或事(寫作中常被視為最卑微,然而卻是最強悍的現實背景)……而「她」在「對岸」——於是,一切已然在旅途中,在寫作的僭越中,在未來無限的可能性中,在從「東」到「西」的互為「主客體」的「存在」之必然連結中……
——《東西》是什麼「東西」?「東西」是什麼意思?
——須留意的地方是,關於「東西」的論述,以上五點,是從便於展開推論的角度,邊論述,邊舉例,而非把詩集《東西》裏的詩歌截然按其內容分門別類於每個小論題之下。事實上,在我引用到的各種詩例中,它們皆為獨立的「東西」,內涵於各個論題之中。
——語言多麼神奇,如上,我寫的是《東西》之「辯」而非「東西」之「辨」,然而,你是否也聽出了關於《東西》的 「東西」之「辨」弦上之音呢?
2010年12月
(註:此文已刊《百家》。但由於寫作時間較短,未盡完善,日後再擴寫補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