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註冊,結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讓你輕鬆玩轉社區。
您需要 登錄 才可以下載或查看,沒有帳號?註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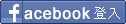
x
大笪地──很令人懷念的地方。又或者它其實是一個隱喻:平民,沒有權威,不必拘泥,雜亂但有生氣,包羅萬有...
我是第一次探訪大笪地的,理應有見面禮。我就將最近一篇刊登於《小說風》第2期(2008年4月)的作品貼上(原本一些文字效果在貼上之後沒有了)。
梁品亮
《細說》
(一)
韓風
我曾經捉弄一位女同學。
我對同學甲說──這不是很有趣嗎?
我對同學乙,丙說──你猜她的反應如何?
我對同學丁,戊,己說──來吧,玩一玩又何妨?
我對同學庚,申,壬,癸,子說──就在數學堂,好嗎?
我對同學丑,寅,卯說──以她為目標最好。信我!
我對同學辰,巳,午,未,申,酉,戍說──請你們幫忙!幫忙!
我回覆同學亥──她不算漂亮?這沒關係。她是乖乖女,很文靜,從來不與我們說話?就是這樣才過癮!
那年的數學堂上有廿三對脈脈含情的眼睛集中在一位專心聽課的女同學身上。不消半堂的時間,女同學感到混身不自在,蛋面紅了,如塗了胭脂。二十二張嘴巴因為惡作劇的得逞而偷笑。
我還記得妳那對看著我的十分倔強的眼睛。當時妳可以做的,大概就是以一對倔強的眼睛作防衛。妳看著我的時候我把視線移出窗外。校園牆外的木棉樹稍稍動一動。太陽剛好經過它的頭頂。那一刻木棉樹想也不想便抓住一把陽光,當作帽子戴上了,慢慢把帽舌拉下,將眼睛及半張臉藏起來。那天每節課堂都滲透了那株木棉樹的形象。
下課後,妳頭也不回,箭步離開課室。我也急步緊跟其後,眼睛追蹤妳的身影。其他參與惡作劇的同學留守課室,大聲笑起來。這時風刮起了,灑滿陽光和打上條條欄杆影子的走廊把妳的校服裙輕輕揚起的情景記錄下來。妳本能地用手將裙子安撫下來。一剎那,風,還有妳的表情都腼腆起來。
高雲
你錯了,留在課室的同學亥並沒有因為那個惡作劇而笑過,在你和江雪離開後他只是一面茫然。沒有人比我更清楚同學亥心裡所想的是什麼了。
江雪
日後我曾經想過如果我遏止那股衝動,安坐書桌前,沒有跑出課室的話,往後的事情就不會沒完沒了。甚至我經過走廊時,沒有那一陣風,也許是另一個結局。多年後,他仍提起我裙子揚起的情景。他真胡塗,竟把淺淺的粉紅色當作白色。我沒有糾正他。我害怕再一次流露當年腼腆的表情──這幼稚的表情與我現在的年紀不相襯。
韓風
第二天妳坐在同一張書桌前。
我把眼睛移出窗外。校園牆外的木棉樹一動也不動。天知道它是否滿懷心事。自此直至我中學畢業,木棉樹都不能回復我戲弄妳那一天的老樣子。
高雲
戲無益。
江雪回來的那一天,同學亥整天都神不守舍,他把眼睛都放在你和江雪身上。他也許期望與你的眼神相遇,把一些心事傳遞給你。可是你卻老是抓著那株木棉樹不放,眼睛沒有離開過它。同學亥生氣了,覺得你有事情隱瞞他。
江雪
耐人尋味的是接著那一天你們兩人都沒有上學。又之後的一天,班主任喚來你和高雲的母親。她們都哭了。當日你們都要留堂,將校規抄了一遍又一遍。
我下課後沒有回家,只在學校的圖書館流連。當時的女同學都愛看岑海倫、亦舒的小說,又或者是三毛的作品。我從不喜歡她們的東西,書中的感情都很陌生,至少當時我的感情並非如此。直至今天,我們的小朋友都看甚麼呢(如果她們想看的話)?張小閑?深雪?對我來說,她們的文字世界與我更為遙遠。我不是說這些女作家不行,只是我相信感情世界是不能複製的,無論小說裡的故事多麼動聽,賺人熱淚,都不足作參考。親身體驗的愛情,無論多麼糟糕都遠勝一紙虛擬的童話式的愛情──我當時相信是這樣的,此刻仍是這樣想,所以我從來都不看小說。那一天的我心不在焉,從書架上取下一些書本,匆匆看了一眼又將它們放回原位。也許那一天我要找的是你經常坐在一旁(你永遠都不太合群,那次出主意捉弄我是一次例外)讀的那一部大部頭的書。
之後,我乘巴士的時候,果然碰上了你們。
韓風
英國女作家Beryl Bainbridge最近提及自己花了三十年仍未讀完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這是甚麼一回事?要麼世間有些事情是不能自拔的?要麼我們不想了結一些事情?我與妳相識大約有二十五年──四份一個世紀吧。如果用生命作計算單位的話,就是由精子與卵子給合之後,呱呱落地,吃奶,長大,入學校讀書,畢業後開始為事業而努力,也許已經有了愛侶,有人生的另一個故事...真驚人,二十五年的時光可經歷的事情原來是這麼多的──可是如果用了結一件事情的時間來作衡量單位的話,則二十五年竟然太短,一閃而過。時光這東西真奇妙,也太使人沉迷,以致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不過,這些問題也許已經不重要了。如果妳認為當年我在圖書館經常讀的那一本書是如此重要的話,那麼我不得不告訴妳我看的其實不是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現實世界發生的事情的確不像電影一樣──我不是藤井樹,妳也不是藤井樹──我們都不是《情書》的主角。我看的是姜白石的詞集。如果要將我對妳的感情強分階段的話,那時就是一個屬於“詩”的階段。姜夔的作品是深情的,譬如他在《長亭怨慢》寫到「樹若有情時,不會得,青青如許」。當時這一句深入骨髓,現在則覺得他有點孩子氣,不是現代人的感觸。他不正是道出愛是會帶出哀傷的嗎?樹因為戀愛而有生命力,所以枝葉青青蔥蔥。不過,愛的本質就是傷害,葉子豈能不枯萎?但情就是這麼奇怪的東西,當春天再到來的時候,樹還是青青的,延綿不斷的戀愛使生命對死亡說不。人有時連草木也不如,因為我們太害怕受到傷害了。我懷疑現代人太過沉迷速度了,對於細水長流的愛情不以為然。所以在他們心坎裡的樹木永遠不能長出枝葉。我想到我們的肉身都有腐朽的一天。軀殼也不存,何來載負慾望?為了把慾望永遠流傳下去,我決定強將它與身體分離。我是否在那一刻開始認同柏拉圖式的戀愛,將一切的愛欲都留在精神的層面。如果這是事情的原初面貌的話,對於姜白石詞句的感觸無疑使我走上一條狹窄的路,換句話說,他的作品就是感情的毒藥。
第二次考試失敗之後,我決定放棄入大學讀書的目標。那一刻,我對妳的感情默默地步入第二階段──“小說”的階段。世界的中心已經由純粹的“情”走向不能捉摸的“情節”了。為了增添情節,我們插入多少迂迴又或者是多餘的枝節。一夜間,彷彿一切都是段段的敘事。
我們為甚麼會永遠讀不完一部小說?A L Kennedy在一篇名為A Perfect Possession的小說寫道:「當愛上一個人的時候我們便會受到傷害,因為愛是一回痛苦的事情,這是它的本質。今天,我們就算不知道那些痛苦是否會過去,我們也得承認愛一直傷害我們。」妳太過害怕受到傷害嗎?也不盡然,可能是我對妳的傷害太深,妳不得不放棄。又或者一如Anais Nin在她的日記引述Henry Miller的說話:「由於欲望往往與我們的意願朝相返的方向走,它迫使我們愛一些使我們受到傷害的事情。」妳的聰明使妳體會這一點,所以妳無視自己的慾望。還是Jelinek看透世情,她在Greed說:「愛並不推倒隔膜,正如老生常談,它築起隔膜。」這面牆使我們永遠等待,裹足不前。對妳我是沒有怨言的,因為我也有責任。我們是否太沉溺於受到傷害的感覺?
高雲
我永遠都記得大學二年級那一年的二月十四日。在那個極具象徵意義的日子妳忽然主動約會我。我與妳看電影、燭光晚餐,之後到我在學校附近租下的小房子。妳說要在那裡過夜。當我還未及想到是否快了一點的時候,妳已經將衣衫脫去。我還記得妳的動作是如此的利落。妳曲手到背後,將胸罩除下,一對乳房隨著脫掉內褲的動作搖晃。更令我想不到的是妳竟然連避孕套也準備好了。我們沒有擁吻,也沒有愛撫,妳剛躺在床上我便按耐不住,想立即進入妳的身體。以第一次而言,我也許顯得笨拙(避孕套也是妳替我戴上的),但我花足氣力,一心只想將妳帶往生命的高潮。妳未幾也真的叫喊起來,不斷擺動下身,配合我的動作。不消三分鐘我便排洪了。這大概是我人生中最長的三分鐘。我拔出的時候避孕套差不多滿瀉了──我對妳的愛意......一直以來我都有一個假設──男人排出的液體與他對那個女人的愛是成正比的。我沒有驗證我這一套理論,因為我只曾與江雪幹過那回事。不要笑我是無膽匪類。我只是害怕我的理論經不起考驗──我排在別的女人身體內的比注入江雪的更多。
風,我永遠痛恨你,也永遠妒忌你!我想到如果我未曾遇上你的話,我的生活是否會更完整一點。甚至你沒有出主意作弄江雪的話我們三人走的路便完全不同,也更好過一點。完事之後,江雪驀地坐在床邊,房間的燈光暗淡,我在她的背部留下的指痕若隱若現。當我仍然亢奮之際,她竟對我講一則故事。我但願永遠沒有聽過這個故事,或者能把它徹底忘掉。可是它盤桓的根卻纏著我的心房,而且天天生長,彷彿沒有枯萎的期限。她說之前某個星期天,你和她看了一齣電影(高達的《斷了氣》)。你不懷好意的送她回蒲飛路的宿舍。由於是星期天,她大部份同學都回家了,所以明白你的用心,特意叫你偷入她的房間。不久你開始動手把她的衣物脫下。她還記得你的手是如何的輕,態度是百般的溫柔。在昏暗的房間裡,你們赤裸裸的,互相擁吻,將身體疊起來。你把她的雙腿掰開,在黑色的陰毛中央之處解錨,進入了她身體的深處,將緩緩的暖流留在她的體內。窗外的風與樹葉的細語剛好蓋過你們喘息的聲音。她坦白地說我使她想起了你。我的笨拙就是你──韓風──所欠缺的東西。江雪說你太懷!
Fuck like Wind!她當時心裡想的定必是這句話。
那夜我打開了窗,想將宛如燈泡的月亮關掉,卻關不掉。就在那一柱戇直無聊的街燈下江雪用模稜兩可的手勢截停了一輛的士,頭也不回離開了。觸不著看不見的風盤繞著那街燈,不時逗弄旁邊的樹葉,發出唦唦唦的聲音。無法安睡的我偷看自己的小弟弟,原來亢奮不已的他變得垂頭喪氣!我開始明白跑得再快也並不代表獲得勝利。世間有些事情總是沒有終點的。
江雪
韓風太自私了!你有想過我會喜歡柏拉圖式的戀愛嗎?我不喜歡,從不喜歡!從不!你的自以為是使我受到傷害。為了你,我對高雲說了謊話。那天晚上我們看完電影之後,你送我回大學的宿舍。那夜同學大都回到家裡,宿舍人少得很。我叫你偷入我的房間,你卻說不。我用懇求的語氣對你說在我的房間裡有一份禮物等待你拆開。你竟然推說下次見面的時候(我們約定下次的見面日期為二月十四日)要我帶給你。今天我不妨坦白告訴你那份禮物其實就是一個避孕套。只要你走入我的房間,就算你不要這份禮物我也不打緊,我送給你的就算是我的貞操也沒所謂。我哭了一夜。從那天起,我就害怕受到傷害,是你的傷害,刻有你的特徵的傷害──你忽冷忽熱的態度挑起我的好奇心,鬱鬱的神情、屢次的考試失敗惹起我對你的憐愛,使我立下決心要與你一起。你卻以猶豫不決來報答我。你就像一個貪得無厭的小說作者一樣,每每在故事應當結束的地方徒增懸念,又或者輕易地一筆轉到其他的情節,使得事情沒完沒了。
韓風
江雪再上學的第二天,我在路上遇上了你。我們一路保持沉默,直至距離校門二百米或半分鐘的時候,我與你不約而同地說:逃學。
你笑了。
我們當天幹的事情大約如下:
0900:譚公道。
在撐起墨綠色帆布下的大牌檔,你叫了及第粥,我口袋裡的錢不多,所以要了米王和炒麵。你再叫了一碟炸両,慷慨地與我一起吃。我們就是這樣地吃了一頓豐富的早餐。
1000:明月戲院
我們決定去看一場早場。我已忘了是甚麼戲,只記得是大人或老師嚴禁我們看的電影。在入場之前,我和你認認真真的把紋有校徽的領帶解下,摺好後收起來。經過這個“儀式”之後,我們都覺得自己長大了。
1215:海心公園。
我和你躲進一處隱閉在嶙峋怪石的地方,藉著剛看完那部電影的餘威,拉開褲鏈,把那話兒拔出來,比拼誰的偉大。你說你的是龐然大物,我說我的虎虎生威。在爭論不休,忙著把褲鏈拉上的當兒,你認真地說誰輸了便當盡力為勝出的完成一個心願。是甚麼心願?我問。
1315:馬頭圍邨。
你提議到銀馬車試試西餐,由於我根本沒有三十元在身上,結果你跟我到馬頭圍邨一棵大大的細葉榕下吃車仔麵──布滿了牛腩、豬大腸、雞翼的粗麵。
1430:麗宮戲院。
這天我看的戲超出過去半年的總和,而且不用分毫。午後人不多,買中座的票不難。戲的名字是《朱絲汀與朱麗葉》,步出戲院之後,我和你再起爭論──你覺得朱絲汀比朱麗葉漂亮,我卻不同意。大概是由於名字的緣故吧。在中二的英國文學課,我們讀的就是《羅密歐與朱麗葉》。我曾幻想自己是羅密歐,我的女人當然就是朱麗葉。所以在我心目中她是世上最美的。我不得不補充一句,麗宮戲院自始成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戲院,有不少電影在那裡看。
1715:啟德遊樂場。兒時在我心目中荔園是香港的狄士尼樂園,它的地位是今天的香港狄士尼樂園都不能取代的──即使它在多年前就已經關掉了。不存在的事物總有不可替代的魔力。不過我更常到的是啟德遊樂場,因為它較近我住的地方。那天我們玩了跑得慢慢的摩天輪,並不驚險的過山車,馬兒都褪了色的族轉木馬等等。與你一起坐在旋轉咖啡杯的時候,我察覺四周的人都列嘴大笑大叫,圍在場外的人好像也想把自己的快樂分給我們,我伸手想把這些歡樂又友善的快樂抓緊,可是杯子旋轉的速度愈來愈快,那一張張臉變得模糊,那些浮游在空氣的快樂漸漸變得不真實,無論杯子走到那裡去,我眼睛看得清楚的就只有坐在對面的你。那就是我們玩的最後一個機動遊戲吧。不知是因為玩旋轉咖啡杯的時候你與我有著同一種感覺(我指的是那種捉不著快樂的感覺),還是你開始擔心逃學的後果,你與我一樣都是沉默不語。我們經過那一排接近出口的哈哈鏡時,我看了一眼,兩人在鏡中都是扭曲的怪模怪相。這個畫面我銘記在心,不能忘掉。
我也不清楚我們是否在那天建立起我們之間的友誼,抑或你我是共犯,總之日後我們就常常走在一起。你也開始將買來的二手Penthouse毫無保留的與我分享。
這次與你一起逃學是空前絕後的,因為之後你再沒有試過了。與我不同,你基本上是一個守規矩的人。自從那次逃學之後,我開始直接叫你高雲,以取代不帶感情成份的同學亥。在這之前,就只有江雪有此待遇。每次獨自逃學的時候,我都懷念你。
高雲
你當時問我的心願是什麼。我記得我沒有答你的問題,因為我想你早已知道答案了。我只是轉身用我最快的速度往前跑,你立即隨著我跑。我長得比你高,腳比你的長(因此按比例我的那話兒應比你的長),所以比你快。你決定用另一種方式跑:將雙手提起,像是想飛,並非按直線跑,而是忽左忽右呈S型的路線。我總想阻礙你的路線,所以我也按你的走向改變我的方向。我雖然始終領在你的前方,但由於並非按直線跑,加上要回頭看你的動向,速度也慢了下來。結果我們都跑得筋疲力竭。
江雪
你們都執著誰長誰短的問題。我永遠不會給你們答案,因為重點不在長或短,核心的是...你們都知道的...
高雲
上星期我再到海心公園一次。每次在那裡留連的時候,我都禁不著發自內心的微笑起來,尤其是走到怪石嶙峋伸出海邊的一處。那是我和韓風犯下原罪的地方,是我們少年情事棲居過的伊甸園,在那裡我們的慾望坦白地流竄。我們不但在那裡的隱蔽之處比拼長短,還一起看二手的《閣樓》雜誌。妳還記得嗎,我們學校每逢星期五的早會特別長,白髮花花的簡牧師以不純正的廣東話講解《聖經》的道理。他曾提到阿當夏娃在伊甸園吃下禁果,犯了原罪。我不禁想到我們的伊甸園裡發生的事情更為複雜。複雜的原因是除了夏娃之外,還有兩個阿當。如果愛是一種特殊的原罪的話,我們三人的所犯下的大概並非一加二等於三那麼簡單。相信是以幾何級數地與日增長吧!我和韓風把這個“秘密花園”與妳一起分享。所以是我倆給妳身上打下原罪的烙印的。我還記得第一次帶妳到那裡的時候,就在準備回家的那一刻,妳忽然說要鬥快離開公園的大門,語音剛落,妳便拔足狂奔。我和韓風趕緊追上去,不久我便追上了,與妳的身影十分貼近,風卻始終落後在我們之後。不知他是故意的,還是這是他的習慣,他開始將雙手提起,像是想飛,以S型的方式忽左忽右地跑。妳看著他的怪模樣笑起來,不自覺的模仿他的動作,雙手不停地拍動,彷彿想與風在公園的小徑上交叉飛翔。我站在路中心,一動也不動,只默默地看著你們在我身旁盤旋。
韓風
也許因為我是巨蟹座的緣故,我跑起來的時候總像一隻螃蟹,不能走那怕只是一段短短的直路。又或者這是我一種理解命運的方式。為了理解命運,我喜歡在往事裡打轉,東找西尋,突然與過去某一時刻或片段斜向地相遇,就像是螃蟹的走路姿勢。我總是假裝向某一方向後退的樣子,卻忽然以相當快的速度前行。
我們三人的命運就是在以上那種前進和倒退的交替之中構成的嗎?我想只要我們都向往著同一個結局,我們就脫不掉這種進進退退的命運。在大家命運交疊的時候,我們都不知所措,因為在這情況下真實是複數的,那怕是同一回事情。例如當年我與江雪看完電影之後送她回宿舍那件事。那時我正要面對第二次大學入學試。由於我還是處於“詩”的年代,所以我總壓抑那股渴望將自己的激情注入江雪肉體之內的衝動。那一晚我們難捨難離,我終於偷入了她的房間。看到她放在檯面那套《追憶似水年華》我頗為吃驚,因為她向來都是不看小說的。我總覺得她不喜歡小說所營造出來的“真實”。小說太愛曖昧模稜的感覺,但又同時專注人類的行為和動機的複雜性。在矛盾重重之下,小說將太多的東西拒之門外,執意要從雜亂的人生歷史中篩選出合理的記憶。現在回首往事,我也不清楚自己“小說”的年代是否就是濫觴於那一刻。
江雪那夜變得野性,故意讓唱機哼出輕聲的挑情音樂。在唱機和我的眼前,她扭動蛇腰,身體隨著音樂的流竄而轉動,將衣物一件一件脫下來。她這個脫衣舞孃的形象好不陌生,使我疑惑,不知所措。可是小風的思想在這時卻單純得多,只顧將頭枱起來,漸漸說服我將嘴唇毫無節制地吻遍江雪的身體。以往的克制只得靠邊站,乾巴巴地看著我把她推到她那張燙熱的單人床,開始用身體五肢探索她最迷惑我的地方。毫無疑問,進入她的身體的剎那是無比快樂的,那種只可以是從一篇與你心靈契合的文學作品所帶來的快樂所能比擬的快樂。江雪不住的搖晃身體,一如大海中航行的火船──雪白嬌小的火船。我將陰莖如解錨一樣放下,想將眼前這隻撩人的船停下來,泊在這個只有我和她兩人的宇宙的中心。已是慾火高漲的江雪那一刻沒有忘記早已準備好的“禮物”,將抵著我胸膛的手移開,從床頭的抽屜取出一個避孕套...
我常覺得以往發生的事情並非是直線而行的,每每在某一決定時刻因為某些事情而改變它的軌道。所以往事給我們的歷驗或感覺是零碎又不完整的。我們無法預先得知過去的事情的轉折處,甚至是事後亦然。完整感覺的缺失使我們更渴望那個已經失去的完整整體,徒勞地嘗試將過去的碎片重組。事隔多年,此刻我在你們兩人面前重組那夜所發生的事情,心頭竟躍出姜白石那句“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的詞句。也不盡然,也許是那種“恨入四弦人欲老,夢尋千驛意難通。當時何似莫悤悤”的懊悔。究竟是江雪說得對,又或者是你還是我的版本接近真相?我想這已經不重要了。何況這個世界有一種叫做讀者的生靈,他們會在小說這孤獨世界裡選擇,那怕是作者覺得是歪曲原意或愚蠢的選擇。所以,越來越多聰慧又老練的作者拒絕為自己的小說寫出結局。我們都是另外二人的故事的讀者,我們都千方百計想選擇大家的結局。在生命的某一刻,我們與那個結局可能只有一步之遙,但還是功虧一簣。因此我們的故事永遠沒完沒了。
高雲,我其實沒有戴上那個避孕套!對於當時的我來說,這東西是一個隱喻,它代表了退縮、裹足不前,帶有土星在星相學上所代表的遲滯及破壞力量。是那種當我們釋放自己身體時,突然把我們的靈魂從肉身窸窸窣窣地拉出來的力量。它把我們身體慾念所寄居的十數毫升或幾十毫升的液體約束起來,變成眼睛看得見的實物。我徐徐地把陰莖拔出來,但拒絕江雪為我戴上避孕套。一件本來要發生的事情就在沉默之中戛然而止。我並非不滿她的謹慎,女人在完全明白與她上床的男人之前必須要小心,而她們是永遠不能完全明白男人的想法。也不是害怕“搞出人命”,我想當父親或者找個地方把孩子打掉並非天塌下來的事情。只是我當時不知道自己能付出多少來回報江雪。我明白江雪的細心及體貼,她肯定知道當時一無所有的我不能再把她的肚子弄大。我們的愛,我們的膽大妄為、不顧後果的衝動,那怕有十足的生命力,也不能改變這個世界。一種莫名的感覺使我拒絕了江雪的避孕套。這種感覺也有避孕套的相同功效,而且過之而無不及。
當我沿著蒲飛路離開的時候我想起了你在海心公園停下腳步,看著我和江雪一起在小徑上奔跑的經典又永恆的樣子。我覺得我已經無力再跑下去了,要停下來,路上就只有江雪一個人胡亂地四處跑。我笑起來,覺得一種負擔離我而去,路旁惺忪睡眼的野草在穿上沉悶暗啞銀灰色外衣的欄柵下微微點頭,就像對我說:對啦!對啦!對啦!當然,往後的日子我發覺我想錯了,原來那種負擔只是換了另一張臉而已。
直至第二次放榜之前,我再也沒有見過江雪。
自那一天開始,我對姜白石的詞句感到很陌生,牠們再不能引起我的感觸或寄託。我第一次覺得詩的軟弱無力,所以開始親近小說。在孤獨當中,我沿著小說複雜又不老實的情節塑造自己的故事。我當然悔恨自己在那天晚上拒絕了江雪的避孕套,不讓慾望把身體推向她陰道內更深遠的地方,甚至因此而得以開花結果。
江雪
我一直將兩腿張開,想讓你棲居。
日後我明白一個真正相信愛情的人是象徵性的,也就是一首詩。因為對於一首詩而言,一切都只不過是一種象徵。詩與生活的鴻溝來自破碎又撲朔迷離的現實。每當想到這裡,對於現實主義詩學我便感到可笑。兩個人的相愛使他們的宇宙膨脹起來,想把一切都容納在內,包括拒絕和忍耐。可是負擔過重的愛令人不能停留在一直構築的生命之中。
你不是曾經說過在精神的愛情與身體的慾望兩者之間就是愛欲,而愛欲是它們的拯救者。愛欲使我們張開眼憧憬將來。可笑的是,我們憧憬的其實是原來就有的東西──那些曾經垂手可得但已經消失的東西。所以我和你永遠沒法獲得救贖。
大概終結才是保持清醒的最終提示。
韓風
上星期我曾經與江雪見面。黃昏的過度渲染使蘭桂坊塗上俗艷的姿色。我沿路而上,在一間酒吧門前停下來,左右流盼店內的環境。店內的客人不算多,只消一刻便認出江雪了。她仍是那副模樣:黑色的外套,內裡白色的襯衣,解下胸前的兩顆鈕扣,很自覺地流露一股“女強人”的“氣質”。不待我走入店內,她推開桌上的筆記型電腦,向我揮手。
她一定是為了準備第二天的結案陳詞──她正忙於那起比肥皂劇更富戲劇性的爭奪家產訴訟案件。
「你何不把這“奪產迷案”寫個劇本?」江雪的開場白。
「人類的確是墮落了,言語交流再不重要了,“真實”都是建立在白紙黑字之上,可是寫出來的“真實”太多又太令人眼花撩亂。哪一張遺囑才是真的?不過這不重要了,因為我們有律師,他們都是語言的魔術師──法律條文就是他們的道具。我們正身處一個自我放縱的年代,放縱得連真實與虛假都懶得想。也許這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意識,畢竟虛與實的問題總使人頭昏腦脹。」
「你別借題發揮了,要在我面前道德說教的話,省掉吧!」語畢,江雪把酒杯裡的酒一飲而盡。
我用沉默回應了她。
「好了。我受夠了你的冷漠。你始終覺得二奶手上那份遺囑是假的,我替她爭取就是不道德。你要明白法律上的理解是另一回事。遺囑的真偽不是由你和我決定的。」江雪用律師的口吻說。
「妳那天晚上說的。」我說了一句在律師面前顯得愚笨的話。
「是嗎?」 她不經意地說。
「做愛之後的妳最老實。這點──江雪──妳知道嗎?」我說了一句在女人面前顯得愚笨的話。
江雪用律師的智慧回應「幸好不是“黑與白”的。說說罷了。」這時她的手電響起來了,她看了來電顯示一眼又把它放下。
「是他吧!快回覆。」
「不用了。這晚我鐵定是你的。」江雪斬釘截鐵地說。
「妳真懷!」
「當你脫掉我的內褲時,韓風就是一個比我更懷的人。你身體上每顆細胞都是孬種。」江雪開始執拾枱上的電腦及文件。
我笑了,把酒精混進身體每顆不懷好意的細胞裡。
第三街的寂靜彷彿成了蘭桂坊喧鬧過後的慰藉。
「妳消瘦了!」在床前我看著江雪說。
江雪模仿我的語氣,搖頭晃腦地唸著:「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我雖然明白她在戲仿中學階段的我,但覺得那黑色行政套裝的確束縛不了她的蠻腰。
我把江雪的衣物脫下,面貼著她溫暖的胸脯,手在她身體上摸索不同的敏感地帶。這時她的電話響起來了。江雪看了來電顯示後把它放下了,然後把雙腳輕輕的纏著我,摩擦我的皮膚。不久,江雪的電話再次響起來。我正要伸手關掉那手機,可是她卻接通了電話。
「我忙得很(我的舌頭正試探她的小腹),還得準備後天的case(她強忍著舌頭誘發的酸軟的感覺)。今天看來要晚點走(我嗅著她的脖子)...我也想與你一起,可是...噢(我開始舔她的陰戶)...打翻咖啡了...(我進而吻她的陰唇)...都怪你不好,使我分心(我輕輕點頭),當然是你的錯(她埋藏平時女強人的語氣,用嬌憨的聲調說。我再次點頭)...這晚你想要我?(我雙手上下搓揉她的乳房)...好吧,讓我這部慾望機器滿足你吧!(我雙手的動作開始急速起來,就如錄影機按了快進鍵)...你解開褲帶,退開它...聽話吧(我輕輕搖頭說不),是的,把內褲也退下,雙手按著那話兒,想想...do it now...呀...(我的舌尖觸動了她的陰核)...oh...(我已經舔濕了她火燙的陰核)...oh......yes...get in(我進入了她的體內)..yes...」
江雪
你牽著我的手走入一幢唐樓──你的房子在三樓。每次當我走入你的房子時都會深深地吸一口氣。我總覺得那裡四處都是你的氣味,是那種追求快感的氣味。你的工作間就在房子的一角,貼近凸出屋外的騎樓,堆滿了大部份還未讀完的小說。書桌前是兩隻墨綠色窗框的大窗子,每片都有八個格子,仿佛要把外面的世界精確地切割成規規舉舉的方塊。你告訴我你寫東西時總愛把窗子推開,好讓街道上小巴的剎車聲肆無忌憚地從騎樓闖入屋內。你愛煞這些聲音。
那夜我那帶著濃厚放縱口音的呻吟聲響遍西營盤第三街某間房子(代我向你的鄰居說聲對不起。好嗎?)。透過輕薄的手機,我將這些聲音傳到麥當奴道某房間內。這夜,兩個男人在同一時間將精液排出體外,流向不同的終點。如果在這一特定時空的確存在著一位讀者的話,他或她也許會猜測推動這些精液的力量的分別在於一方依賴幻想的幫助,另一股則是性質原始的慾望。
韓風
當妳離開之後,我有些失落。我不明白妳的動機。我彷彿曾經和另一男人同一時刻與一個女人一起做愛。我不習慣三人同床。我一向以為自己至少在某一時刻獨佔了那個女人,深入她體內,把內裡另一個男人驅逐出去。昨晚我才猛然覺悟自己在任何時候其實都只是與他分享同一女人。當我射精的時候,也感到他把體液釋放出來。
索然無味。如果是一個孬種的話──我就是失敗的孬種。
高雲
那夜當我把精液排出之後,我氣喘喘地推開軟若無骨的披子,走到窗旁,拉開繡上複雜又精細花紋的窗簾,飽覽一夜維多利亞港的景色之餘,將身體左右搖晃,使小高變成一支指揮棒,指揮隨著時光流動的景象。江雪從電話傳來的聲音使我相信雖然她的肉身缺席,但靈魂卻在場。她把靈魂交付給我,我因此排出的精液比我在她大學宿舍第一次排的更多。接著又是一夜無眠。
你們再一次刺痛了我。我又再次感到自己呆呆的站在公園小道的中央,看著妳們互相交疊奔跑、追逐。風,為甚麼你的步伐總是往後退的。離群又沉默寡言的你總在令人意想不到的時刻想起捉弄別人的點子。這次你是否像當年一樣想捉弄人,只是今天找我作對象。
江雪
對不起,雲。這次的主謀是我。風,是不知道的。我也是當你打電話給我的時候才靈光一閃,想起來的。
Irigaray說過女性與男性不同,她們性快樂的原則是自我享樂及複數的。女人一直觸摸自己,任何人都不能阻止她們這一行為,因為她們的生殖器是由兩片持續接觸的陰唇組成的。因此,在她們身體裡,早已是成雙成對的,但不是分成兩個個別的東西,它們彼此擁抱。至於你們,我指男人,生殖器是一條柱狀的陽具,所以你們性方面的樂趣是單數的。女人的生殖器是用“唇”來形容的,作為隱喻,它指的是身體的另一器官,它能說話,不論是甜言蜜語、惡毒的咒語、粗話,但更多的時候是沉默。可是男人的卻是一種“工具”而已,是“功利主義”的,它有思想嗎?我相信沒有。我不得不佩服人類選擇詞語的天分,也欣賞當中的直率──男人的“工具”要經常使用,否則會失靈。你們過度的苛索顯得合情合理。不過,工具始終是工具,我難以想像你們是否真的得到快樂。更何況你們要的是單數──你們只要自己的快樂。同學亥,不,高雲,還有韓風(我必得立刻補充一句:排名不分先後。你們不要胡思亂想),你們明白嗎?你們總是互比長短,要我作選擇。你們給予我你們的愛與慾,我也以我的愛與慾回報你們。正是我們的愛與慾以及想佔有對方的意志使大家的關係糾纏不清,沒完沒了。我曾經想過要終結,所以我首先選了穩健的你,接著我改變主意,想要當時一無所有的風,誘他走進我的房間,將貞操獻給他,但他卻錯過了機會。我痛恨他,於是與你走在一起。可是恨意始終不是抗拒愛欲的最大公約數,當他離開香港的時候,我卻想和他長相斯守。當我告訴他會找他的時候卻又捨不得你。我與你一起找他,想告訴他我的最後抉擇(我已應承你的婚約),結果發現自己一直都在想他。打算離開之時,你楚楚可憐的樣子使我把自己的身體再次給你。這是與你最後一次,我堅決地說。風那時卻又放棄了。也許我們的愛的確同時在我們之間築起了一道牆──永遠無法跨越的障礙。看了Irigaray的書之後,我領悟到快樂應該是複數的,你們就像我身體的兩片陰唇,加起來才是一個完整的器官,負責生殖、製造安慰和快樂的身體一部份。我選擇了你們兩人!
高雲
Irigaray是婊子,妳不能相信她的說話!
韓風
同學甲是班內的惡霸,個子高,力又大,加上大家都說他的兄長是黑道中人,所以都不敢惹怒他。妳還記得嗎?那天妳的面色特別蒼白,誰都知道妳的身體不適。直至妳白色的校服裙開了一朵血紅的小花,我才恍然大悟。放學的時候,以同學甲為中心有七八位頑劣的同學(同學丁、壬、癸、子、寅、辰、辛?)在妳的座位圍成一圈,笑得猥褻。我想也不想的走上前,發覺他們在妳的書包內搜出一塊衛生巾。我怒不可遏,一個箭步後,拳頭就不偏不依的落在同學甲那長滿疙瘩的鼻子上。接下來同學丁、壬、癸、子、寅、辰、辛一擁而上...看著同學甲掩著那個比平日更加醜陋的鼻子的可憐相我就禁不著想笑──笑的代價就是一隻牙齒和滿身的瘀傷。我相信我和同學甲在那天所流的血不比妳的少。妳用好奇的眼睛看著我,沒有說出半句話來,只顧用手帕抹去我面上的血,接著輕按我身上各處發瘀的地方。我看著妳的蛋臉以及當妳俯身時露出的乳溝(妳發育的時間比別人早),竟惹起生理反應了。在進一步胡思亂想之前,高雲的支援到來了──紅汞水、包紮用的紗布和關德興跌打油(他永遠相信名牌)。在把我“修補”之後,高雲把自己的外套徐徐除下,遞給妳。那一刻他是那麼細心的,使妳不能拒絕他的好意,立刻把它圍在腰間,遮著裙子上的污跡。回家路上,三條拉得長長的人影是那麼靠近的,卻沒有交疊起來。自始我們成了三人行。
當晚我夢遺了。今天不妨對妳直言。
接下來我們都為自己的目標而努力:
你:課本及會考天書。
我:麗宮戲院、萬年戲院、樂富戲院、國際戲院、大華戲院、快樂戲院、華盛頓戲院、倫敦戲院、域多利戲院、荷李活戲院、明月戲院、普慶戲院、嘉禾戲院、凱聲戲院、麗聲戲院(排名有分先後)。
妳:課本及戲院(前期)、戲院(中期)、課本及會考天書(後期)。
高雲
「你說:我愛你。我說:留下來。
我差點要說:佔有我。你卻說走吧。」
你還記得這兩句話嗎?是杜魯福的《祖與占》。我想那個“你”大概就是片中的其中一位男主角Jim,而“我”就是女主角Catherine。我嘗試用你思考的方式,將“你”擴大成“青春”、“女人”、“愛情”、“藝術”...等等。片中三位主角流露的青春又不負責任的力量,既創造又破壞他們三人未來的生命面貌。這股力量深深吸引我,畢竟我不是這種類型的人。說回《祖與占》,其中一個情節是Catherine約Jim在七時到咖啡店會面。Jim七時零五分到了,不見她。他想到像她這樣的女子會準時到,而且只等一分鐘便會離開。他結果坐至七時四十五分離開。之後Catherine八時才到。姍姍來遲。兩人都沒有時間觀念(大家都不樂意受束縛?)。我想到“無悔”就是這回事了。我們與“她──無悔”相約,卻遲到了,當我們以為錯失機會而放棄之後,“她”就來了。換另一角度,“無悔”姍姍來遲,也錯失了與我們相遇的機會。於是一連串的機會的錯失。至於另一男主角Julie則是一個有時間觀念的人,會用一個大沙漏計時,提醒自己。可是這並不代表他無悔。他想“守時”,但沒有努力使身邊的人“守時”。所以最終他失去生命中兩個最重要的人,只得獨行。無悔本來就是不守時的,我們與“她”約會──緣木求魚。你或許說得對,生命的本質就是各色各樣的後悔。
電影要麼與現實的情況相差太遠,要麼又太貼近。那些把自己的生活“電影化”的人實在愚不可及。我不知道我不喜歡看電影的原因是否與此有關,只能記起打從《祖與占》之後便不喜歡電影了。直至今天,我仍無法理解你為甚麼為了看電影而荒廢學業。
韓風
在接受第一次考試失敗的那一天,我同時與你和江雪興祝你們通過大學校園的門檻。我們在太平山山項,看著維多利亞港兩岸。你考入了建築系,所以當時眼中所見的都是未來一幅一幅的規劃藍圖。你說要在海港構築一條橋,因為建築是把人類拉近的科學;你說要建立一所博物館,因為建築是記憶及藝術的先鋒,你說要設計一個寬廣的文化廣場,因為建築是不同文化差異的守護,你說要為大眾平民提供優秀的居所,因為建築是社群的母親...你說得有條不紊,並不激動,大概是因為你永遠都不會將自己的感情盡露的原因,可是你卻是十足的躊躇滿志。我多麼希望你當時說話是熱淚盈腔的樣子,這對於我這個失敗者而言是莫大的鼓勵。是你使我第一次從建築想起“存在”這一個哲學問題。如果建築是一種語言的話,那麼人的存在便是透過這一沉默的語言而得以實現。你更使我聯想到關於語言的墮落問題。建築是沉默之子,它不懂說話,卻在在傳遞故事──人間的故事,藉著這些故事,人類的經驗展示出來。這就是一種能夠穿透身體及心靈的語言。那一天的維港兩岸尚有一點空間,流露生機。今天的建築物自說自話,喋喋不休,不願意與別人有真實又深入心靈的溝通。是的,我曾經站在一幢高聳的建築物前,它的玻璃外牆使它拒絕了暖和的陽光,變得冷冰冰的。建築物的升降機大堂前一塊雲石刻有你的名字,說明你是這一商業成就的總設計師。
高雲
香港只有地產,沒有建築。
畢業之後我花了幾年的時間去理解一個生存道理:只有職業,沒有專業。懂得這個道理的人會比較接近成功。我當然成功了。
不要抱怨香港的建築物醜陋、沒有感情。我們的幹活不是寫詩,寫小說!我們在建築夢想,香港人的夢都與地產有關,而這個夢想總是盡量把感情因素排除出來。
高雲
風,你剛才戲仿我的聲音及腔調的玩意並不有趣,雖然我同意你的話──香港只有地產,沒有建築。我曾經在一篇論文主張所有建築師都應該以閑逛者的角度來構思自己的設計。他應當喜歡走路,以非線性的方式走路,注意花草人物的所有細節,把一個城市的靈魂都摸熟透了。教授很喜歡我的結論。這信念與其是一種理想倒不如說是一種真摯的愛情。真摯的愛情總是沉重的,與生活有一道鴻溝,因為現實太複雜。你不是說過要寫一些激動人心,不隨俗流的劇本?結果我卻常在電視肥皂劇或戲院放映那些爛片看見你的名字。
我們都是六十年代末出生,七、八十年代成長,九十年代出來社會做事謀生的世代。雖然沒有說出口,六十年代對於我們來說其實是一個隱喻,代表了火紅的革命,對過去不屑一顧,追求理想、自由以及模糊但又彷彿真的會到來的美好的明天。所以六十年代是反叛又年青的。可惜我們出生在這個激情又帶著理想的年代即將過去的一刻,經歷七十年代的理想幻滅及開始萌芽的個人主義,對我們影響最大的是八、九十年代那種精明又對現實世界不對勁的事情漠不關心的麻木,再加上令人窒息的教育制度,我們都成了自我放縱的一代。事業有成使我們安於現狀,不懂得珍惜已經和即將消亡的事物,甚至不知如何去愛一個人。如果覺得現在年輕一代沒有希望的話,我們這一代就是元凶。我們上兩、三代的人也許會對我們說事情也不是如此的,六十年代也不是如此理想,例如在法國紅色革命的戛然而止,還有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但這對我來說並不重要,因為結果還不是一樣?我們還不是都會成為今天的樣子?極其只是使我們多了一個抱怨的對象──我們繼承了前人的虛弱和沒有堅持到底。
江雪
太平山當晚涼風習習,態度溫柔,所以使人失去警覺性。我當時就是憑著對這陣風的感覺向前走──我選了文學院。個半月之後我第一次坐在大學講堂上聽課。教授講的是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我始終想瞭解你當年在學校圖書館常常讀的這部小說(現在才知道你讀的其實不是這部小說)。這無疑是對你的一些執著的解讀,或者更正確地說是一次翻譯的嘗試。之後我明白一個道理:翻譯不是單純的把一種外國語言轉換成自己的母語,甚或不是為了增進對原文的理解為首要目標。翻譯是譯者最細密的一次閱讀,把原作者沉澱在字裡行間的故事編織出來。所以翻譯其實是一種推測,一次考古探險,將一些已經消失的事情發掘出來。不如說說我有關《追憶似水年華》的考古報告。看這本書的那個人是一個沉溺於時光的人,脫離文字之外便一無是處,他的精神就像普魯斯特的身體一樣──潺弱不堪。一個不能掙脫時光的人大概是十分惹人討厭的;不過這也許亦是他的可愛之處,或令人憐愛的地方。也許當愛上這個人的時候,你便得有心裡準備,你們的感情世界就像普魯斯特的文字,綿延不斷,永沒結果,就是從頭開始也只會再添內容,沒完沒了(普魯斯特每次校對稿件時都“不務正業”,只顧添上新的內容)。
在完成“考古報告”的當晚我決定做一件事情,為的是向你報復。不要費唇舌了,我不會告訴你,這是我的秘密。
高雲
我初到日本時,曾被地上綜橫交錯的路軌所深深吸引。當路旁的發聲器「噹、噹」發響,紅白相間的欄柵徐徐落下時,再大馬力的汽車都要停在鐵路前,待火車走過後才可通行。我當時並不知道自己喜歡這情景的因由。
我想火車在日本這個國度裡,是有絕對的特權的。人生而不是平等的,有些人是天生有特權的,而另一些則沒有。例如被愛及施愛的人,前者對後者可以任意行駛他或她的特權。我站在京都車站十樓的架空行人天橋時,所能夠想到的就是這些。那天京都的天氣不佳,雨斷斷續續的落在冰膠的地上,有時勢頭大得使街道迴盪著霹啪霹啪的聲響。黑壓壓又低矮的雲像要把塵世的男男女女看得清清楚楚似的。四處濕漉漉、冷冰冰的,寒氣侵擾人心,總要令人想痛哭一場。
韓風
在接受第二次考試失敗這一事實之後,我決定到日本求學。以香港當時刮起強勁的東洋風而言,我這不失是一個好選擇。我想到要在日本學電影,不過結果我只呆在東京一所叫做外國人語言學校學過兩年日文而已。
我那時在東京的浜松町,八疊的房間狹小又簡陋,與我們在日劇看到的可愛部屋是兩回事。每天除了學日文之外,便是到餐館清洗一大盆一大盆的碗碟。有一天下班後乘搭電車,我從口袋裡淘出早上收到妳的一封信。原來妳已經大學畢業了。妳說本來打算將我的一切忘掉,可是卻做不到。妳很掛念我,想過來看我。妳很文學地寫道:
如果我是作家,我就會僅僅允許我的心靈靠著詩人的意識生活下去,將自己脆弱的、模糊的、充滿欲望的直覺混入所能抓住的你的一切形象,與你天昏地暗的做愛。
尾班車的乘客雖少,但我仍不想這些陌生人看到我流淚,所以我不斷改變坐姿,頻頻假裝打呵欠和抹去臉上的汗水...
半年後我在成田機場接妳。妳的身邊多了一個人──高雲。
江雪
看見你落拓的樣子和那隻患了皮膚病的手之後,我把自己與高雲的婚訊吞回肚內。你強裝平靜,說剛好放年假,本來打算到京都和高山走一趟──工作和學習的關係,你在之前還沒有到過日本其他地方。
結果你仍按原來計劃動身,隨行多了我和高雲。
韓風
高山給我一種陌生的感覺,與那個我度過了一年半有多的忙碌、嘈雜、隔膜、滿地濕漉漉、一排排木制檯凳的東京大不相同。高山市有許多小橋(二十四橋?),其中和合、枡形、中、伐、柳、彌生、不動、連合、萬人等橋跨在宮川河上,天天睜眼看著橋下連綿不斷的流水,不知厭倦。我們住在彌生橋旁的壽美吉日式旅館,據一臉祥和的老板娘(我還記得她的名字是みなみ──南)說,房子虛齡足足二百。我想它大概早已看透世間男女之事罷!旅館是日式的,格局傳統,我們租了二樓三間面對宮川河的十二疊房間,江雪的就在我和高雲之間。晚飯後我留在房間,坐在窗前,細聽宮川河溫柔而節制的水流聲音,回想江雪日間在飛驒國分寺那棵據說有一千二百多歲的銀杏樹前合十祈禱的樣子。一切又回到從前──風吹過學校的長廊江雪的校服裙搖搖晃晃隱約露出白色的內褲與她腼腆的表情好不相襯戲院內白光灑在黑暗的觀眾席上她輕拭眼淚掩嘴低首而笑緊張得將雙唇緊緊咬著一臉正經旁若無人地背誦會考天書的標準答案大學荷花池旁出神地看著那些出神地看著她的烏龜校園幽徑突然跳出來的松鼠花容失色然後露出天真可愛的笑容追逐被她嚇得四處逃竄尾大而不掉的褐色松鼠滿面疑惑地看著Anais Nin的HenryandJune接過我從地上拾起用筆胡亂寫上白石詞句的枯葉後抬起頭閉上眼睛微微張開口唇等待我的舌頭闖入在床上張開雙腿任由我進入她的身體默默看著我穿上衣服開門離去打電話給我卻沉默不發一言因為我前一天告訴她要離開香港到日本讀書與高雲步出機場禁區看見我的時候木無表情。
隔壁房間傳來微微的顫動,不是地震,我知道的,因為接著的是喘氣聲──男人和女人的。月亮當空,將清冷又苦澀的光灑遍宮川河的流水,任憑後者如何流動,都帶不走光影的傷痕。我忽然明白回憶是一個人的個人故事所留下的斑駁月亮餘影。
我關掉頭上的燈,倒頭睡在榻榻米上,感受從隔壁傳來越來越真實的顫動的同時,徐徐退去和服下的內褲,開始自慰。
江雪
我當時站在那棵有一千二百歲的銀杏樹前禱告,希望如此長壽的它會有足夠的智慧給我一個忠告:要堅定不移。我本來到日本的目的就是要告訴韓風我的最終抉擇,準備與他來個了斷(你求仁得仁,不是活該的嗎?),所以我與高雲一起找你。我寄出你在電車裡讀的那封信之後的第二天病倒了。那時我真的渴望你在我身邊,可是來照顧我的卻是高雲。當他將雪白無花巧的白粥端到我面前,我開始感到他才是我生命中的男人。你的愛相對來說太虛無,難以捉摸。不要笑我小女人,太易陷入電視劇或電影的老舊情節了。疲倦使人的思想開小差的同時也令人接受一直就在身邊的“幸福”。舉個例子,大概你沒有痴痴地連續九天將鮮花送到我面前的能耐吧?也沒有記下我所有喜好的細節的本事(高雲,你為此做過筆記嗎?)。惱人的是,當我再見到你的時候,一個小小的念頭卻在我的心裡炸開來,像雪球越滾越大。
大樹沒有給我忠告,他沉默不語。
我相信決定性的時刻發生在我們走到那座橙紅色叫作中橋的時候。我再次提議大家鬥快跑到橋的另一邊──一、二、三──只有高雲拔足!我痛苦地領略到韓風你留在我體內的東西從來沒有離開過。
晚上當我坐在窗旁看著陌生的高山月色時,高雲推門走入來,明顯喝了清酒,解下和服的時候,小高出奇的堅硬挺拔。
我從未如此的樂意給他。背後的原因迷離。
滿瀉。又一次滿瀉。
高雲
.....
江雪
第二天早上,老板娘送來早飯──還有你的信。你告訴我們要先回東京。
當我和高雲經過你的房間時,老板娘拿著你用過的被,看著一塊污跡,莞爾一笑,又不失老練地用英文向我們說早安。
高山駅。終於下雪了。飄雪。
下一站,京都。
再下一站,東京。
又一站,大會堂。在那裡我和高雲在紙上簽下自己的名字。
又再一站,律師樓。在那裡我和高雲在紙上簽下自己的名字。
我們婚後的生活其實美滿,除了從來沒有行房之外。真奇怪,當分居紙簽了之後,我與高雲做愛的次數反而更多。說到這回事,你好像永遠沒有長大,當騎在我身上的時候,你就像小孩子看見新奇的玩具一樣,總是旁若無人,花盡氣力,一心一意地幹。一時又像要把眼前的玩具拆骨,探究它的基本構造。
與你同床一年使我對男人和女人性方面的需要有新的體會,是單數與複數的角力。
韓風
是感情的傷痕使妳走上法律的專業嗎?
江雪
你猜對了一半。簽分居紙的時候我明白一個道理,感情問題是不能用文學作品──包括詩和小說──來解決的,它們只會將問題弄得更加複雜。問題只能用法律來處理。另一方面,相信你也同意,這世上沒有一種叫做愛情專業的東西──假如我們覺得今時今日專業資格是生活的必要條件的話。愛情不能考核評分,也不像知識一樣花多點時間溫習會提高水平。當我取得律師的資格,偶然在肥皂劇片後字幕看見韓風兩個字之後更進一步加強我這個信念──原來我的情緒是可以這樣平靜的。當我們日後在街上偶遇,交換電話,再進而發展性關係的時候,我對自己說路是走對的了。
韓風
妳真的這樣想嗎?
江雪
......
高雲
......
韓風
......
(二)
高雲
我們的關係就像一個三角形,我們各自代表其中的一條邊線。這個三角形並不是等邊的,每條邊的長度並不相等。有時我是當中最長的(但大部份時間都是最短的嗎?),有時是韓風,有時是妳(大部份時間妳都是最長的嗎?),不過任何時候我們所形成的內角加起來都是180度。對嗎?當妳與他最親密的時候,三角形的形狀變得不平衡:你們都變得很長,比我長得多。毫無疑問,當你們交疊一起時,所形成的是一個足以刺穿我心房的銳角。
江雪
我無意傷害任何人,包括我自己。愛欲是一門藝術,而藝術只教曉我們憑感覺走,卻沒有給我們何時停止的啟示。有些事情是不能自已的。我對我們的關係有另一番的體會──是菱形的。我們都想像三人以外存在一個“他者”,這個人渴望愛,所有的愛──朋友的愛,異性的愛。我不清楚他的存在有多真實,因為我看不清他的面貌,當我想抓著他的臂胳的時候,他總是逃脫了。他是幽冥的火焰。
菱形的每一個角都鋒利得足以傷害我們。
韓風
N減2乘180度。
你們還記的這條求解多邊形的方程式嗎?菱形看似與三角形不同,它的內角無疑比三角形的大一倍。可是,兩者的內角豈不都是根據同一法則計算出來?其實,過去我們的關係並不是這樣的,它沒有法則。我們組成的是一個圓形。我們的關係沒完沒了,永劫不復。
(三)
一處會落雪的地方。很陌生。
我踩踏腳掣,把車子停下來。江邊堆積了昨夜落下的雪,一陣帶著寒意的風驟然掠過水面,一朵白雲默默地滯留在高高的天空。收音機播著一首歌:
But what lovers we were, what lover,
Even when it was all over -
the deadweight bull-black wines we swung
towards each other rang and rang
like bells of blood, our own great hearts.
We slung the drunk boat out of port
and watched our unreal sober life
unmoor, a continent of grief;
The candlelight strange on our faces
like the silent tiny blazes
And coruscations of its wars.
We blew them out and took the stairs
Into the night for the night's work,
stripped off in the timbered dark,
Gently hooked each other on
like aqualungs, and thundered down
To mine our lovely secret wreck.
We surfaced later, breathless, back
To back, then made our way alone
up the mined beach of the dawn.註
我憶起了三張面孔,不自覺的哭起來了(原來我早已熱淚盈眶)...
註:這其實並非歌詞,是一首題為Wreck的詩。作者Don Pater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