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註冊,結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讓你輕鬆玩轉社區。
您需要 登錄 才可以下載或查看,沒有帳號?註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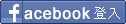
x
鳶飛魚躍的游心禪境─ 評陶淵明《飲酒﹝其五﹞》
魏晉時候,中國思想界進入先秦以後,最燦爛、多元的時代。當時,儒學衰落,道、釋興起,三家鼎立之局已成。後來,三家更呈合流之勢。經過多年論爭,三教互相吸收、影響,士風因而大變。加上,莊園經濟大盛,士人與自然合流,並多以此為題,致使山水、田園之風大盛。被後世譽為「田園詩人之宗」的陶淵明亦乘時而起,《飲酒﹝其五﹞》正是其杰作之一。 正如上言,《飲酒﹝其五﹞》乃於儒、道、釋三家合流之時而作,當中正正蘊含了三家思想的精粹。對此,筆者以為陶淵明在寫就此詩時,應達「鳶飛魚躍的游心禪境」,成就「天人合一」的極致。為方便讀者閱讀,現先引錄全詩如下: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歸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首先,詩之首兩句便已反映陶淵明當下的修為和想法。當時,陶淵明致仕在家,「閑時寡歡」,故終日飲酒,「孤影獨盡」。想當年,陶淵明因不願「為五斗米而折腰」,憤然辭官歸故里,足見其厭惡繁囂的俗世生活。但話雖如此,陶淵明畢竟只是凡人,終須「結盧在人境」。「人境」除指人生活的世界外,但觀乎陶淵明一生,屢仕屢辭,足見他深知人生在世,總不能餐風飲露,終須向現實低頭,故此「人境」亦應指心境,即俗世的、浮沉的官宦生活。由此可見,陶淵明雖能忠於自己,但亦難免俗,其心仍是矛盾、無奈的。 正如上述,無論在現實或心理上,「人境」均象徵繁囂、令人燥動的生活和思想。據此,陶淵明此時應是心煩意亂的,但他竟說「而無車馬喧」。對此,筆者以為這正好反映陶淵明心中仍有「車馬喧」。他於人境結盧,便不難明白他的心自仍存有「人境」、「車馬喧」的印象。因此,他只是慣於車馬而驚於無喧,所謂的「寧靜」只是陶淵明的心所刻意安排的,絕非自然而然,渾無所覺的。由此可見,陶淵明雖未達「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但以上兩句實亦足以反映他對寧靜、安逸的生活的追求。 其實,人境結盧,欲忘車馬,徘徊於現實和自然之間,正好反映本詩所含有的玄學哲思。正如上言,縱觀陶淵明一生,屢仕屢辭,既未能免俗出世,亦未能逍遙江湖,因此儘管結盧人境,卻心繫江湖,耳無車馬,心實未能忘懷。由此可見,陶淵明之心仍是搖擺不定,或出或處,實尚無定案。對此,羅宗強便指出「陶淵明雖偶能達到委運任化的玄學心境,卻因思想底子仍屬儒家,故雖安貧樂道,卻仍難以免俗」。如此矛盾的心情,正好與東晉玄學若合符節。 玄學始於漢末,盛於魏晉,作為當時的思想主流,玄學的核心關懷正正在於「名教」與「自然」的關係,並探求「人」在兩者之間的定位。發展至晉中葉,由於政局已然大定,士人已開始接受晉政權。再加上,東晉偏安亦讓士人愈發輕忽現實政治,務求玄遠的人生。自此,玄學便更強調個體的自覺性,講究人生與自然的合一。此外,自東晉以後,玄釋合流,使當時的思想界及士風瀰漫一股追求安靜恬淡的風氣,期望寧靜致遠的人格。因此,玄學至東晉,其風再變,進一步將「人」從「名教」中解放,講究人生與自然的契合。但人畢竟為人,絕無可能放棄現實人生,因此「現實」與「自然」的拉扯,始終困擾人心。正因如此,文風自亦流露士人對寧靜的自然、淡泊的人生的追求,本詩亦隨即應運而生。 承接上句,陶淵明雖耳無車馬,心實未忘喧鬧之聲,所謂的「靜」乃「心之使然」而已,「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便正能為此作出充足說明。陶淵明自言,能超脫於人境,其關鍵於「心」。所謂「身在曹營心在漢」,陶淵明雖身陷人境,但心卻神游於八荒之偏,故能立於現實之中,游於虛無之外,尋得那「動中之靜」的心境。由此可見,「心」在陶淵明詩中,佔據極其重要的位置,是連繫「真實」與「理想」的樞紐所在,亦即「游心」的體現。 「游心」並非陶淵明首創,先秦道家便已十分重視「游心」的表現。《莊子》一書便曾多次提及「游心」的意思,當中《莊子‧田子方》所言,極合陶淵明刻下之心境。《莊子‧田子方》曾言: 「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
在此,莊子藉老子之言,表達個人的宇宙觀,指出「陰陽交通成和而物生焉」,以為天地萬物本陰陽交感而成,而生死交替,實是無端無窮的過程。由此可知,在莊子眼內,萬物本無差別,均為陰陽之所生,且更相交替,無所謂「開端」,亦無所謂「終極」,萬物齊一而無別,此之謂「物之初」,即形上的「道」於形下世界的具體落實。但眾所周知,如此虛無的境界,絕非凡人肉身所能企及,故莊子又提出,若欲「游心於物之初」,則「心不能困」、「口不能辟」,唯有解放「心靈」,擺脫世間的枷鎖,方能成就「游心之境」。 然後,莊子又指出解放「心靈」,必須「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由此可見,「游心」講求「莫忘莫助」、「自然而然」,回到「物」的本然狀態,無礙於萬物及情感,如此便能心游於「天之高」、「地之厚」和「日月之明」的「物之初」。當然,我們不得不承認,莊子式的「游心」與陶淵明的「游心」有一根本分別:前者棄絕塵世,醉心於道的「虛無」,而後者則心游於動靜兩端,希望尋得那心靈的休息之地。但兩者卻同時重視「心」的虛靈性和超越性,指出「心」是連繫兩地的關鍵,及「游心」對於超越的作用。 對此,明代理學家王陽明亦有一精闢的見解,高揚「心」的主觀能動性和價值賦予的主宰性。《傳習錄》曾語: 「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詩中的車馬喧聲便如王陽明口中的花,「同歸於寂」與「一時明白」並非取決於客觀存在,而在於主體的「心」,「看」則存於人心,氣、味、形、色自是一目了然,「不看」則僅為花開花落的自然之事,於人心亦無半點漣漪,藉此說明萬物由心,突出主體對客體的價值賦予。對此,西哲普羅泰戈拉亦有一言:「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高揚人是「存在」與「不存在」的價值主宰,價值實是在於「主觀的心」而非「客觀的事」。同樣,陶淵明亦主張,以「心」超越客觀事物的形象,並以主觀意識超越客觀制限,達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游心之境」。 接著,陶淵明便交代他的生活及抒發當中的感受。從詩而言,陶淵明致仕隱居後,不獨沒有「車馬之喧」的煩擾,更能享受田園生活的平靜,閒時便「採菊東籬下」,反映其生活的淡泊和幽靜。其實,陶淵明之「採菊」實是饒有深意。 首先,就「花」之象徵而言,可知陶淵明之個性。眾所周知,「菊」在秋末冬初時開放,具有凌霜耐寒、清香飄逸等特性,「凌霜耐寒」喻其不畏嚴寒,不媚俗隨波的高貴品性;「清香飄逸」意即處事低調,不爭豔鬥麗,亦能隨風飄散,風化四方,此又直如孔子所言:「君子之德,風」,足見「菊」確具「君子之性」,故世人亦將之與「梅」、「蘭」、「竹」同譽為「花中君子」。此外,正因「菊花」不媚俗,不高調,故周敦頤於其〈愛蓮說〉亦稱:「菊,花之隱逸者也」,以盛讚其傲岸風骨。綜合上述菊花的特性,可知陶淵明實有意以「菊」況己,說明退隱不仕的願望,和以「君子」自居的個性。但陶淵明卻又明言「採菊東籬下」,則「菊」仍為「籬內之花」,由此可見陶淵明心志淡泊,雖身在人境,但心繫江湖。 其次,再從詩作言,以「菊」況己,實為強化其心中的理想歸處。正如上言,「採菊東籬下」一句,乃陶淵明況己之句,而「菊花」及「君子」終非方外之物,由此可見陶淵明的理想人格,並不如莊子筆下的神人般不吃人間煙火,而是有血有肉的,入世的理想道德典範。但又如上言,陶淵明雖身在人境,但心游方外,「菊花」及「君子」應非其心中所嚮。對此,「悠然見南山」句正可作出說明。 「南山」之意,時有爭論,但若以詩論詩,則「終南山」之說應較恰當。沈從文根據文物,指出由於「商」與「南」的漢隸字形相近,故於漢及六朝,人們時有將「商山」誤稱為「南山」。根據東漢光武帝《以範升奏示公卿詔》記:「自古堯有許由、巢父,周有伯伊、叔齊,自朕高祖有南山四皓」,可見沈從文之說是。據此,沈從文再引申到那四位輔助惠帝有功的「南(商)山四皓」,以為陶淵明實是「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對此,筆者以為沈從文論證「南」實「商」之誤寫,自有其獨到處,但同時,筆者卻以為沈從文的引申義,應有商榷之處。 縱觀全詩,陶淵明既已心游方外,則人境自是虛幻,家國大事亦應已拋諸腦後,否則絕不能處於「游心之境」。對此,筆者以為「南山」雖確為「商山」,陶淵明由此聯想到「商山四皓」亦是合理,但他所想的應為四皓的歸隱之志。根據《史記‧留侯世家》載: 「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 商山四皓憑己力,扭轉乾坤,力保惠帝不失,足見其憂國憂民之心。但他們絕非如伊尹般「治亦進,亂亦進」,而是如伯夷、叔齊般「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寧可歸忍,亦絕不仕不義。由此可見,商山四皓雖有積極為民一面,但同時亦有消極退隱一面,若「邦無道,則卷而懷之。」陶淵明一生屢仕屢辭,天下無道,自是了然於胸,因此儘管其「猛志固常在」,亦不得不接受現實,退而歸隱江湖,忘卻朝堂恩怨。「悠然見南山」實指陶淵明欽仰四皓的歸隱之志。 綜合上言,可知陶淵明雖以菊自況,以君子自居,但無奈時局昏亂,再加上「性本愛丘山」,故萌南山之志。在此,「菊花」的淡泊之性與「南山」的歸隱之志,互相滲透,加強了陶淵明有所不為的「狷者」形象及心中歸向。其實,陶淵明便正如朱光潛所言般,「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陶潛渾身是『靜穆』」,因為「靜穆」正是其理想歸處。 承接上言,可知陶淵明能身處人境,而忘卻車馬,其關鍵在心之所遠,但此僅一心之所造,乃主觀所為,非自然而然。直至「悠然見南山」一句,不獨描繪了陶淵明的理想歸處,亦說明了陶淵明徹底融於自然,完全擺脫人境,其心境亦隨之產生質的飛躍。 根據蘇軾《題淵明飲酒詩後》載,「悠然見南山」本作「悠然望南山」。對此,蘇軾表達強烈的反對,認為若作「望」,「則此一篇神氣都索然」。誠然,「望」與「見」雖意近,但若放於全詩,則確有雲泥之別,陶淵明之心境亦因而變得庸俗。 「望」與「見」均意指客體呈現於主體眼前,但細究兩者,可知「望」實有「看」之意。「看」之古意,乃置手於目上,極目遠望,可知此乃一主動的「尋」。置放於詩,則陶淵明於採菊之時,以悠然的態度,欣賞那充滿隱逸之氣的南山。如此,則自然僅為一可觀賞之物,陶淵明非寄情山水,實欣賞山水而已。既然如此,陶淵明實未達「游心之境」,而僅欣賞「游心之境」而已,與「天人合一」之境更是遙遙相對的。 但「見」的意思則較中性,且有隨機之意,僅指客體呈現於主體眼前而已,絕無尋覓之意。加上,陶淵明之心正如上述,已然脫離車馬繁囂,完全投入自然的安靜之中,而「尋」即身非於此而求於此,因此「望」實未能承接上文。反觀,「悠然見南山」承接「採菊東籮下」,則採菊而後見山,一氣呵成,自然而然,渾然天成,全無刻意之舉。在此,景非人的欣賞物,人亦非自然的欣賞者,彼此平等、滲透,情景交融,營造出閒適自然的氣氛。 再者,「南山」象徵歸隱、淡泊,若作「望」,則陶淵明乃一徹徹底底的狷介之士,人境與自然截然兩分,執著於自然而無視生活,這顯然與陶淵明的一貫形象相背。因此,筆者以為「見」方能完全配合全詩的脈絡,自有為之心過渡至自然之心,將生活與自然融合為一,從人境自然過渡至江湖,全無造作矯飾之處,自然而然,實現幽靜的「禪境」。 唐代王維素有「詩佛」之稱,其詩作多蘊含佛理。觀乎上文所言的自然與生活,王維正好有一詩─〈終南別業〉,能充分說明陶淵明的心理。該詩曰: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垂。 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一句,表示王維出游儘管前無去路,他仍能享受自然的氣息,就像預先安排般,水窮即坐,欣賞雲起於水之端,當中絕無任何斷裂,行動就如行雲流水般暢達,充分反映王維當時心境寧靜,出處自然,隨遇而安的生活態度,實隨意而不失生氣,亦即講究隨緣而不執,活在當下的禪境。 根據上文,再配合「悠然見南山」一句,可知陶淵明雖非釋徒,但其生活態度卻是一致的。當時,陶淵明已然與自然為一,自然即生活,生活即自然,既隨遇而見南山,亦不執於「望」、「尋」南山,全無煩惱和桎梏,自然與生活在其生命中,達到高度的統一。由此可見,陶淵明實已成就幽靜的「禪境」。 除卻南山外,陶淵明的自然之心亦感受到整個大自然的生氣,使全詩產生極大的空間感,引領讀者欣賞大自然的偉大。「山氣日夕住,歸鳥相與還」將讀者的視野與靈感,擴大至更宏闊的景象,由一隅之山伸延至整個自然。怡人的天色使人感到舒暢、寧靜;自由飛翔的歸鳥,為大自然添上幾分生氣。此時,天地、萬物均從其天性,享受自然而然、無拘無束的生活,正如孔子所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如此生活亦正是陶淵明所追求的淡泊和恬靜。 此情此景不獨使陶淵明樂在其中,其心更進而與自然契合,與生靈同感,與萬物共同感受自然所賦予的生命和生活。在此,陶淵明已完全融化於自然之中,感受自然的生氣盎然,感悟「吾與點也」的聖人氣象。面對此情此景,陶淵明便直言:「其中有真意」,而當中真意實正與後世理學家所體會的「鳶飛魚躍」的自然之理,若合符節。 「鳶飛魚躍」一語,本出於《詩經‧大雅‧文王之仕‧早麓》,後《禮記‧中庸》曾對此作出解釋,其言曰: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根據《禮記》所言,可知遠於先秦,先哲已悟道於自然,以為人道源於天道。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生命川流不息,自然而然,自然之道也,非人力、地力、天力、道力所能及。自然之道非離道、天、地、人之外,獨立自存,而是道、天、地、人依其自身律規,自然而為。 對此,朱子亦言: 「鳶飛魚躍,道體隨處發見。謂道體發見者,猶是人見得如此,若鳶魚初不自知。察,只是著。天地明察,亦是著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之細微,及其至也,著乎天地。至,謂量之極至。去偽。」 朱子以為「鳶飛魚躍」正是道體的發見之處。所謂「道體」便正如《禮記》及《老子》所載,源於天地、見於天地的自然之道,萬物因其所生、恃其所長,自然而然,而「不自知」的生命流動,此即謂「天命流行,生生不已」的意思。 接著,王陽明亦據此,進而言及: 「天地閒活潑潑地,無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非道,無往而非工夫。」 王陽明亦認為天地間的生命流動,其流行不息、活潑潑的在於「理」亦即上述的「道體」。「道體」充盈於萬物之中,不離萬物。但於日常間,萬物是難以感知這自然而然的道體,故「道體」之於萬物亦是「不得而離也」。綜合上言,王陽明明言「無往而非道」,萬事萬物皆為道,因此「無往而非工夫」,唯有於日常生活間,以心加以體會、感悟,方能實現和掌握此「自然之道」。 正如上言,「山氣日夕住,歸鳥相與還」所描述的正是四時、萬物的各適其式,本其天性的自然生活。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率乎天性、自然而然便是道體。由此可見,陶淵明於此所得悟的「真意」正是儒家式的「鳶飛魚躍」的道體流行。 最後,關於對「道體」的啟悟,陶淵明無以言之,唯言:「欲辯已忘言」。正如上述,陶淵明得意於「山氣日夕住,歸鳥相與還」之象,雖心有所悟,卻又難以言喻。在此,陶淵明明確提出玄學的方法論─「言意之辯」,以為「得意忘言」正是體道之方。其實,「言意之辯」實非出於玄學,而是《莊子》,不過由於玄學提倡本體論,便正式將「言意之辯」作為其探究玄道本體的方法論。「言意之辯」的內容,據《莊子》所言: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在此,莊子將「言」與「意」喻作「荃」與「魚」及「蹄」與「兔」,確立兩者的工具關係。「荃」與「蹄」即捕魚及捕兔的「工具」,其價值只在於捕得「魚」和「兔」。一般人於捕得「魚」和「兔」後,便會忘記「荃」與「蹄」的存在。由此可知,「言」只是表「意」的器具,人於「得意」後自亦「忘言」。「欲辯已忘言」便正好呼應「得意忘言」之意。 同時,「欲辯而忘言」亦有強為之言的意思,陶淵明於此實有意,極言道體的偉大。據《老子》,有關老子對「道」的看法,其言曰: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縱觀老子對「道」的描述,其「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的特性和地位便正如上述的「天命流行,生生不已」的「道體」,亦即陶淵明所言的「真意」。在此,老子直言「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極言「道」的偉大。由此可見,陶淵明面對自然的偉大,除感觸不已外,實亦敬服不已。 總結全文,陶淵明生於魏晉之世,深受儒、道、釋三家影響,其思想底蘊雖貼近儒學,但其本性卻又接近道學,而其境遇又促使其人生具有釋家的影子。從《飲酒﹝其五﹞》一詩,可知陶淵明致仕回鄉,但仍身處人境,唯其酷愛自然的本性,促使其心游於人境與自然之間,成就道家的「游心之境」。正因陶淵明深愛自然,故能從欣賞自然,進而融入自然,將自然與生活合一,再達到釋家的禪境。最後,已與自然合一的陶淵明,深深體會到自然之美及生命的偉大處,故能超脫言語的藩籬,掌握儒家式的「鳶飛魚躍」的道體。最後,三者融合為一,完成「天人合一」的至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