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註冊,結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讓你輕鬆玩轉社區。
您需要 登錄 才可以下載或查看,沒有帳號?註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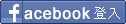
x
〈身體〉
(1)
不知怎的,最近總是發着同一個夢。
全身赤裸,躺在一個黑色的空間內。
其實說是「躺」,是絕不準確的說法,我們往往會躺在一些實在具體的物件上,例如床、沙發、大腿。但那裏卻是虛浮的,無論用手如何到處亂抓,總不能抓得住任何東西,身體彷彿被一隻無形的手托着,無重地飄浮在一片無盡的黑色之中。但是飄浮總有點微微的浮動吧,而身體那刻卻能安穩、一動也不動地平躺着。所以我只好用「躺」來暫阻說明那時的情況。
其實我可以隨時坐起來,但是我的身體卻反對這個想法,只願意靜靜地躺着,一直一直的躺着。由於家中的熱水爐是儲水式的,儲水量又少,往往很快便沒有熱水了,所以每次沖涼都是匆匆忙忙的,胡亂洗擦一下便完事,從沒有留意過自己的身體。想不到現在觀察起來,這具日夜相隨的軀體卻令我有一種參觀博物館的獵奇感,身體各部分就彷似展品,任意地讓我這個第三者細覽。
本來平伏的腹部已經壟起成沙漠中的小沙丘,像被一陣陣風吹過,肚皮早已泛起一疊疊若隱若現的皺紋。也許在這層充滿疊痕的沙丘下,早已埋藏了不少腐屍與早已逝去的生命。雙腿腫脹起來,肉緊貼着肉,互相黏稠地磨擦,融為一體,彷彿瞬間退化成一條魚尾。而最吸引我駐足觀賞的,是那天生擁有某種強烈象徵意味的陽具。它像一隻喘氣不止的老狐狸,終日避藏在草叢內,等待着牠早已捕殺不到的獵物。
這令我想起初生時的經歷。根據科學研究,人類大腦負責記憶的部份要等到兩、三歲才完全成長,所以一般人對於三歲前的記憶大多數十分模糊,更遑論要記住出身時的記憶。但是,我出生時的畫面確實在我腦海裏歷歷在目,每次回想起,我也能記起當時的聲音與氣味,甚至護士帶着小小的紅色耳環也記得清清楚楚。當我由一道黑色的隧道出來,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強烈的白光,照得我很不舒服。當我開始適應時,才發現自己的半身還被擠壓在陰道內。那時,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這身體不是我的。我看看自己的手,皺皺的,每一根手指還不能自如地開合,小小的腹部連着一條血紅色的吸管。這就是我的身體嗎?怎麼會顯得如此陌生?想到這裡,我不禁哭起來。然後,醫生便成功把我從母體分割出來。
我忘記了說,在夢中,躺在我身旁的,有兩個赤裸的女人。
她們熾熱的身軀緊緊地貼着我,彷彿已成為我身體的一部份。但是我卻沒空仔細觀察她們的身軀──她們的手更惹我的注目。手正溫柔地撫摸着我的陽具,當中沒有半點情色的意味,就像魚和水一樣,她們的手彷彿本就該活在那裏。她們溫柔的動作彷似一尾孔雀魚轉身時牽起的陣陣漣漪,一派溫婉與綺靡。
就在此時,身體下那隻無形之手突然收緊,我開始缺氧,全身的肌肉繃緊,血液好像快要從血管迫出來。我耳邊清晰地聽到骨骼與骨骼之間的磨擦聲……
咯咯……咯咯……
我從夢中醒來。
(2)
雖然它很困擾我,但是我沒有向人提及過這個夢。這種夢,不知怎的,總有一點神秘性、禁忌性,總是叫人難於啟齒。也許,城市內每個人都與我一樣,每天心裏都藏着這麼一個黑色的夢,在五光十色、人來人往的街道獨自穿梭着。但是,我們寫專欄的卻比一般人幸福,我們可以將它打碎、重組、裝篏、染色,然後把它好好包裝,把原本血淋淋的肉塊,端上桌子給人享用。這就是我一直迷戀寫專欄的原因,無論哪一類的專欄,無論是多低俗、多少錢、稿費多不準時,我都喜歡寫。這種快感就好像赤身露體地在大街走着,但偏偏所有人都看不到。
我把這個夢寫在一個已經連載了一年多的色情小說專欄內。那天專欄的題目是「阿當的綺夢」,話說阿當由於縱情聲色,年到三十已經不舉,但有一晚卻夢到前女友夏娃與莉莉絲同躺在床上與他覆雨翻雲。當阿當醒來,發覺自己的陽具竟然勃起了,於是再去砵蘭街「起雙飛」,大戰三百回合云云……
而事實上,如果用綺夢來形容我那個黑色的夢,卻是不太合適的。因為那個夢對於我來說,完全沒有半點情色的意味,每次醒來後,我的陽具也不會因她們的身軀而勃起。
我總是覺得,那個夢是關於身體與身體之間的思念。
從前人們總是喜歡把身體與靈魂分開來,把它們視為組成一個人的兩大元素。我不知道這種二元論的劃分是否合理,事實上,現代的科學研究早已證實情緒和思想全都是大腦不同的反射區做成的,而被從前的詩人熱情地歌頌的愛情也許亦只是毫不足道的分泌物。但把一個人分為身體與靈魂這個原始的想法,卻深深地吸引着我。
我有一個毫無證據的信念:身體與靈魂事實上是兩個互不溝通的個體。血肉的身體固然沒法理解靈魂哲學性的思考,而靈魂亦沒法了解身體溫熱的思念。靈魂儘使早已忘記那兩具身體的存在,但身體卻依然對它們念念不忘。
於是,我做了一個毫不合理的決定 ── 找回那兩具被我(正確來說,是我的身體)思念着的身軀。
(3)
結識阿夏的那個夏天,她半年後便要結婚。
那年夏天,太陽總是高高的掛在城市的頭上,狠狠地追蹤着、照射着每一個快要昏掉的行人。那時我畢業了兩年,還沒有找到長工,只好兼職到街上派傳單。我站在旺角的地鐵站的出口,一邊被人潮與熱浪衝擊,一邊派發着旅行社泰國遊的消暑推介。就在這時,在中文系畢業之後唯一間中聯絡的阿德打電話來:「有水上樂園的免費票,有興趣嗎?」
於是,我把整疊傳單直接掉進垃圾箱。
當我趕到水上樂園,阿德與他的一班朋友早已在入口等着我。阿夏便是他其中一個帶來的朋友。她個子嬌小,一頭黑髮及肩,穿着一件薄薄的白色緊身襯衣,胸部顯眼地突起,內裏桃紅色的泳衣若隱若現。她穿着一條短短的藍色牛仔褲,一對有點褪色的平價膠拖鞋,背着一個小小的背包,活像一個剛剛畢業的高中生。但是後來才從阿德口中得知,她比我們大兩年,已經在中學當了兩年教師。
由於我和阿德的朋友完全不認識,所以大多數時間只是跟着大隊走,間中和阿德閑聊幾句,其他人也沒有刻意和我攀談,我亦樂得靜靜地聽着他們的嬉笑,陪着笑幾聲,悄悄打量着名夏。而阿夏只顧和她的朋友嬉戲,好像完全注意不到我的存在。
不經不覺,已經黃昏了,眾人都已經筋疲力盡,但阿夏卻依然精力旺盛,像一個不想回家的小孩,不斷拉着眾人,嚷着要玩「海浪體驗」。但是眾人都紛紛擺手,只想坐坐休息一會。我見眾人也沒有什麼反應,於是冒着被拒絕的風險,裝着輕鬆地說:「我也想玩這個,一起去好嗎?」
阿夏看着,好像從前打量一下我的五官,然後笑一笑,點一點頭。
由於差不多日落西山了,人流也逐漸減少,我們很輕易地便游到水池的中心,等待人造海浪的到來。她的頭髮早已濕掉了,幾條髮絲濕漉漉地伏在她的臉上,我很想用手把她臉上的頭髮撓到耳背後,但瞬間又為自己這個想法感到不好意思。氣氛有點怪怪的,於是她主動打開話匣子:「你唸書還是工作?」
「畢業了兩年了。」
「在做什麼?」
我有點不好意思,苦笑道:「派傳單……」
「不要緊,」她拍一拍我的肩,語重深長地說:「年青人,只要用心,就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我看着她一臉稚氣又一臉認真,覺得有點好笑,感覺上好像被一個小學生在勸勉一樣。我正想反駁,但是水面卻漸漸騷動起來。
「浪來了!」我興奮的叫道。
人造海浪從遠處徐徐湧過來,我們腳下一邊踏着水,一邊伸高雙手歡呼。海浪越湧越快,越打越高,彷彿處於真正的海難當中,但是我們面對這種人造的死亡威脅卻毫不驚恐,反而把歡呼聲提得越來越高。阿夏不小心喝了一口水,急忙拉着我的手,而我也下意識地把她攬住。她略大的胸脯緊緊地壓在我的胸口,我們的心臟彷彿突然緊貼在一起,我清晰地聽到她每一下心跳聲。卟、卟、卟卟、卟、卟卟卟……
一個人造海浪打來,我們便立即被捲到水底的漩渦之中。
那晚,我們被波浪捲到床上。我們拼命掙扎,大叫,慌亂的手在水底中隨便摸索,隨便捉緊一些東西,又隨便放手。波浪衝擊在我們的身上,牽起白色的浪光,點點水滴在半空中定格,凝固了半秒,然後徐徐落在我們的慾望之上。我們互相廝殺,翻身,搶奪對方口中的最後一口氣,直至力竭,直至喘息不止。自從那夜開始,我們便自這一張床轉到那一張床,由旅店的那一張床轉到家中的這一張床。她結婚之後,我們這種關係還維持了好一陣子。
「你還在專欄寫色情小說嗎?」阿夏翻開被子,用腳探索床邊酒店提供的紙拖鞋。
「沒有了,色情版那邊裁員,我轉去寫世界異聞版了。」我看着阿夏穿上內褲,才發現原來已經不是她最喜歡那種白色喱士花邊款式。
「世界異聞版?這是什麼來的?好像沒有聽說過。」她的聲音十分驚訝,但是她卻沒有看過來,繼續忙着找回她的衣物。
「世界異聞版是專報導一些世界不可思議的奇聞,例如水怪呀、外星人呀、未來人呀,那些沒有證據又言之鑿鑿的報道。你有聽過上個月俄羅斯發現只有手掌般大的外星人屍體嗎?這便是我們行家的一則傑作。其實這些報導很多時都是我們這些專業寫手創作出來的,到外國網站找一張有趣的圖,然後圖下的文字便任意發揮。」
「也很好呀,你從前不是常說要當作家嗎?這也算是向作家邁進一大步吧!」她穿胸罩時胸部的曲線在半空劃了一個半圓。
事實上,我不覺得這工作與作家沾得上半點邊兒,但也不願反駁她,於是便轉轉話題:「阿彬現在還是這樣忙嗎?」
「還不是老模樣,經常到大陸工作,一個月回來一個星期……」她頓了一頓,然後繼續穿她的妄服,冷淡地回答我。
阿彬是阿夏的丈夫,已經結了婚四年,雖然我與他沒有見過面,但是從阿夏的片言隻語中猜測到,他應該是一個好丈夫,但是缺點就是長期出外工作不在家。還未結婚前已經是這樣了,難道我現在才抱怨嗎?阿夏曾經與我這樣說過。
我很後悔提及阿彬,我本就不應該提及他,他的名字使我們陷入深不見底的沉默。
阿夏穿好衣服,對着鏡子整理一下頭髮,準備打開房門離開。正要離開之際,她好像想起了什麼,回個頭來對着我說:「不要介意,也許你今天太倦了吧!」還未等我回應,她便轉身關門離開。
嘭!
就在她關門的一瞬那,我感到軟弱的陽具無力地顫動了一下。
(4)
招牌的左上角寫着「腳底按摩」四個小字,中間畫着一個腳掌的圖案,而腳掌內用LED燈排成一張笑臉。燈,閃着閃着,笑臉彷彿對着我這個猶豫不決的人,投以一個意味深長的微笑。
我看着這張笑臉,又確定旁邊的街角沒有人走近,然後匆匆走進這座唐樓。
「如果在腳底下有張笑臉,即是代表……」
當一起走出公司的大門時,阿龍便把面靠過來,笑吟吟地說。
之前在色情版工作的時候,就只有阿龍一個同事,所以與他比較熟稔。他每天都會去色情場所替性工作者拍照,然後拿回來創作出千篇一律的故事。正所謂「近水樓台」,他常常在這些地方出入,少不了會自己身體力行,試驗一番。有一天,當我們下班時,他笑吟吟的對着我說。其實腳底按摩亦有正邪之分,他說。如果腳下有笑臉的就代表有姐妹在這裡「搵食」,他說。前日放工時發覺這裡轉角就開了一間,他說。
他把臉再靠近我多一點,他呼出來的暖氣把我的臉弄得癢癢的。
「不如,我們到那裡試試好嗎?」
這裡就是阿龍上次帶我來的地方,沒錯,應該就是這裡了。
這幢唐樓的梯間十分昏暗陰涼,與街外的炎熱喧囂形成強烈對比,有着一種不真實感。梯間窄窄的,只夠兩個人並肩而行,地面有一點濕濡,每當我走過通道外的垃圾筒,總會嗅到一陣魚腥味。牆上的灰都開始剝落了,已看不到本來的顏色,只見每層也貼上一張泛黃而破爛的告示:「不要隨地小便」。鐵閘的油漆也差不多脫盡了,只能隱約見到像青苔般的微綠,而不少的人家門外也煞有介事地貼着一張便條:「住戶人家,請勿騷擾」。不知怎的,一切一切,竟然令我想起陰道。
我一直沿着扶手走上去,目標是在四樓。
其實我也不太肯定是否在四樓。上次阿龍走在前面,加上我又是第一次到這種地方,根本不敢隨處亂望,只顧低着頭看着自己的腳尖。進到房內,時間也胡裡胡塗地過去,半點細節我再也說不出來。幸好見到木門上掛上一個與樓下一模一樣的招牌,我才放心下來。
叮噹。叮噹。
我按下門鈴,但等了一會,門內還是沒有任何反應。於是我繼續按着。
叮噹!叮噹……
不久,門內開始發出一些微弱的聲音:腳步聲、開門聲、踫撞聲、清脆的玻璃聲、水聲、拖鞋聲、越來越近的拖鞋聲……
「老闆,那麼早便上來?」
只見木門打開,一個女人不情不願地探出頭來。
這個女人大概……對不起,事實上我不太懂猜測女人的年齡。在我心目中,女人只分為年青和不太年青兩種,而她明顯地是屬於後者。一頭長長曲曲的金髮在頭上散開,掩蔽着半張臉,眉毛和眼睛差不多也躲到後面,卻清楚看見一道深刻的魚尾從眼角展開。臉頰蒼白,嘴唇十分乾燥,吻上去的感覺應該會是十分粗糙的。
看着她的棉質背心與運動短褲,我就知道,我大概來早了一點。由於現在工作比較彈性,可以自己安排時間,所以我總是喜歡用晚上來工作,而把早上的時間用來作一些日常雜務。例如到銀行入錢、看電影、到書局,我都喜歡早去,因為早上總是比較少人,不用和別人爭先恐後。但現在看來,這個邏輯對於嫖妓方面是完全不合適的。
「妳是……莉莉嗎?」
「啊,原來是熟客介紹……」
「不,我之前來過的……」
「是嗎?我認人一向很差。」
「我可以一會兒再到來……」
「不,現在就可以進來,這才叫專業嘛!」她擦一擦眼,唇邊還有點牙膏跡,微笑道:「只要你願意。」
(5)
莉莉的身體沉靜地躺在紫色的床單上,更顯出她皮膚的白晢。她的頭髮略作梳理後,變得貼服了點,散在臉上,雙手墊在頭下,有一種說不出的倦意。她的身型豐腴,每一吋的肌肉都覆蓋着厚薄不一的脂肪,形成變化多端的曲線,有些地方像個綠草如茵的小山坡,有些地方卻像波浪起伏不定的海灣。
她躺着,一動也不動,間或傳來一陣陣沉沉的呼吸聲。她,睡着了。
我們甫進房間,她便脫下背心,嚷着要替我洗澡。我退後一步,道明我的來意:我只想她赤裸地躺着,什麼也不用做。她本來是不肯的,怕我會幹些變態的事,又怕我會偷拍放到網上。最後,我答應加錢,她才不情不願地躺在床上,但卻瞬間熟睡了。
她的身軀令我想起童年時,服裝店櫥窗內的模特兒玩偶。童年時,樓下的小商場有一間街坊的時裝店,售賣着一些便價的內地衣服,深受一般屋邨太太的歡迎,而我媽媽也是熟客之一。那間時裝店有一個習慣,就是每個月的最後一日都會把櫥窗內模特兒玩偶的衣服全都脫光,然後翌日新貨到來,才把最新款的衣服換上去。而模特兒就只好衣不蔽體地挨上一個寒冷的夜。
每到那些晚上,我都會找個藉口逃出家門,然後坐在櫥窗外靜靜的看着。月色淡淡地照射在無頭的模特兒玩偶身上,使她們平滑的肌理顯得更加蒼白,有一種說不出的詭異。她們有時伸高雙手,有時把手垂在腰間,但是無論她們什麼姿態,手永遠都不會長一分,腰總不會粗半點,她們就像一片永恆的永恆,讓我有一種說不出的安心。
那時候,我看過一本有關希臘神話的書,皮格馬利翁的故事最令我感動。皮格馬利翁是希臘著名的雕刻家,有一次,他用象牙製作了一個女性的塑像,並愛上了她,給她起名為伽拉忒亞。自此之後,他每天都會獨個兒留在工作室,與伽拉忒亞談天與擁抱。愛神維納斯非常同情他,於是決定為這件雕塑賦予生命。自此皮格馬利翁與伽拉忒亞便幸福地生活下去。每次看到最後,我都會恨維納斯多事。有了靈魂的伽拉忒亞會令到原本永恆的身軀老去,而老去的身軀終必會腐化。何必為了片刻的歡悅而失去了永恆的擁有呢?
每次想到這裏,我都會叮囑自己不要為那些模特兒玩偶起名,因為名字好像總是與靈魂有一種微妙的關係。身軀就是身軀,根本不需要任何名字。
看着莉莉的身軀,想起那些模特兒玩偶,我的陽具不經不覺勃起了。
臨走前,莉莉好像對我有點依依不捨,攬着我的膀臂笑道:「老闆,什麼時候再來呢?要多多來啊!」看來我這種客人──付錢受別人睡覺的怪人,對她們來說是蠻受歡迎的。
我笑了笑,把手臂抽出來。
「不會再來了,我明天結婚了。」
我知道,那個叫阿當的男人不會再來。
(6)
海地負心漢離奇死亡
祭師聲稱全因肉體重
(1-3-2014世界異聞版)
海地近日發生多宗離奇死亡事件,多名男子在家人離奇暴斃,而根據病歷,全都沒有隱性疾病,經過法醫剖屍研究,亦找不到真相,只能把「心臓突然停頓」作為死亡原因。
但海地多名祭師聲稱,這些死者的肉體過重,皆因他們全都犯了奸淫,背着自己的妻子有外遇。
「這些男人由於犯了太多罪,肉體積存了太多的罪孽,於是引致過重的問題。」祭師烏都達充滿信心地說。他認為由於肉體越來越重,而靈魂卻越來越瘦,於是不堪負荷,最後決定拋棄自己的肉體離去。
當記者問及死者靈魂的去處時,烏都達沒有正面回答,只拋下了一句難以理解的說話:「肉體在地上盛開,在地上腐爛;靈魂在天上飄散,在天上安坐。大家都去了自己的所屬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