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註冊,結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讓你輕鬆玩轉社區。
您需要 登錄 才可以下載或查看,沒有帳號?註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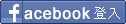
x
本帖最後由 thk 於 2014-3-2 23:27 編輯
又是一個無風的下午,姐拉著我走到堤岸的石堆找尋魚人的行蹤。我們躺在父親留下來的漁艇,等待海水像起皺的抹布從岸邊緩緩滑落。我們仍是很快越過欄杆,但這次大家都沒把膝蓋撞腫。姐捲起寬闊的褲管手夾著拖鞋走在前面,只是跨了一步,兩條曬得黝黑的腿便立在一塊大石上。她看來十分興奮,就像以前父親駕着艇把我們載去直木島旅行時的心情一樣。那時候,姐和我都是第一次到外島旅行。直木島的中央長了棵阻光的樹,大約佔了島的一半地方。每逢中午,樹頂的枝葉會吐出層層沉重不散的雲霧蔽住上空,有時雲裏還打著閃電。我們趁著父親下船後偷偷坐上一輛無座位的觀光巴士。巴士駛往山頂繞過一圈便下山,沿途經過了巨樹附近。樹下沒有車站,只有兩尊光著身子的半魚半人的木雕安置在路旁。導遊說魚人是沒有男性的,當地人的先祖都是以捕獵魚人為生,所以便索性將樹底鐅空成了魚人博物館,也是島上唯一的景點。我很期待館內會充滿著美麗的魚人標本,不過當天恰巧是博物館的休息日。我們最後在原來的碼頭找回了父親。他沒有如常地打罵我們,純粹脫下身上的水褸綁在姐的腰間,一言不發地把我們抱上了艇。姐蹲下來的時候,她的雙腿像剪刀般被生硬地分開,我瞥見裙裏同時也散出了淡淡的褐色鱗片。
後來我才知道那是她的初潮。
回家後嫲嫲與父親吵了一頓,彷彿她對姐在巴士上忽而迎來初潮感到非常討厭,說著日後屋裏的椅子和被單和衣物等都會開始忽而被弄髒。我漸漸憂慮兩年後會否像姐一樣突然在家外迎來初潮。
姐偶爾會停下來回頭望向我。我知道她不想重提島上的事。我曾在晚飯時問父親何時再到直木島旅行,他打了我一巴掌,我的右臉頓時發著如頂上燈泡般的熱光。母親與父親馬上又鬧了起來。嫲嫲莫名其妙地罵起了鄉語,接著夾起餸菜拿走碗筷走進廚房。姐也累得扣著自己的手臂在飯桌上倒頭大睡。我忍住牙痛吃完碗內剩餘的米粒,仍未了解大家不再談及直木島的原因。
隔天凌晨時分,漁艇慢慢地把父親駛離了家。
姐哼的笑了一聲,在我面前輕易地提起右腳,橫著雙臂裝作稻草人的姿勢,然後別過身又跨前一步,石上因而遺留一對濕潤的腳掌。我彎低身子,雙手壓著它們才勉強跟了過去。手心還被刺入了沙。我們沿著旁邊的行人徑走向沙灘,姐不時在亂石間撿到一些可於日常碰見的物品,昨天她便發現了一片斷分成丫的銀白尾鰭。它不及手掌般的大小,薄的,而且乾枯,擱在陽光底下,會顯露出半透明的細密紋路。姐謹慎地將它放入早已喝完的果汁瓶裏,她解釋這是魚人來過的證據。我記得母親的刀也常常黏著幾片輕薄的鰭和鱗片。
沙灘上的人不多,大部分人更不是在游泳。灘上遺留著幾個仿如戰時的地雷坑,有人在這兒打了場快樂的仗。在灘的盡處我們該會看見一個細小的窪,那就是嫲嫲提及過的魚人棲息地。周遭的石堆將窪隱藏得很好,一塊扁平的大石剛巧掩住它的上方,她說村外的人根本找不著它,他們只能找到老鼠或野狗。姐平時很少帶我走到灘頭,我通常喘著氣坐在灘上等候她。大概五分鐘後姐便回來,她不曾向我透露那裏究竟活著甚麼,有時候她手上會多拿著一個殘缺的螺殼然後擲向我,我摸著頭隨意便把它丢在灘上。
「又白走了吧,你們嫲嫲隨口講個故事就胡亂相信。」母親在廚房狠狠地揮刀砍著砧板。
的確,嫲嫲說故事時是喝了點酒,難怪會夾雜些鄉音。她總在同一天內把故事多說一遍,特別在晚飯之後,而故事中的漁夫也不期然地被她改成了父親。當中的內容或者有點出入,但嫲嫲始終不肯把故事說到最後,往往在魚人被父親的水歌吸引悄然登上了船後便乍然停止。噹噹噹。母親在魚腮斬了幾刀,它的頭與身體還是頭一次碰上對方,所以彼此都沒有交談。我敞開了冰箱,那兒依舊讓人感覺涼快。母親警告過再玩冰箱便將我活生生的打死。我發覺箱內還留著午飯時餘下半尾的白凍魚肉。我不喜歡吃它,因為那是母親親手劏開慘白的魚腹抽出腸後煮成的。她把方才支離了的魚放進飯煲,我認得它是抓住紅繩在房窗上吊的鹹魚。它死的時候,我們一家都並不在場。當日母親從碼頭集市買它回來的時候,它早就失去了生命。我曾聽見姐嘗試問它有否在海裏遇過魚人。它張著崩裂的嘴,似是吐出了最後的氣來回答,它生前老是碰見魚人,還不只一個。姐戳著魚身,繩子正在或快或慢的晃動。另外,它還目睹過魚人是怎樣吃掉我們的父親。
當然,那些都是姐存心發出來的聲音。
有了月事以後,姐已經習慣跟靜物談話。嫲嫲一直認為父親離家失蹤的原因是由於姐那突如其來的初潮,她深信在海上來潮是會惹來魚人的,因此也和母親對罵過幾次。每當姐來潮的時候,嫲嫲都立刻在廳中脫去她的褲子及內褲,接著將她困進浴室至少半個小時。姐一向都會不禁沉悶,喚我隔門與她聊聊電視上播放著的節目情節。聊久了她便開始跟浴室內的靜物說話。最初是她慣用的牙刷。
「你還要怪責自己多久,這事根本與你無關,我的牙肉本來就比較敏感才會容易流血。」
近來她好像愛上了房裏剛剛撿來的銀白尾鰭。它睡在果汁瓶底,姐入睡之前都會拿起了瓶在月光下仔細地看。看了一會便伸向我的眼前,齒狀的切口彷彿如根蔓延在半透明的幕下,她彈著瓶底,使清晰分明的紋路形成了獨特的脈搏。我一點也不覺得它美,所以關燈後便懂得閉上眼裝睡。它真的好美,看到吧,它屬於魚人的一部分,對嗎?明天再去可能撿到更多,呀,我們又忘了要去阿姨那裏。
由那時開始,我就患上了失眠症。我以為姐入睡之後我也可以同時睡去。她是沒有說話,然而我聽見她的牙正在對話的聲音。它們咯咯的響,像要埋怨姐平日都不太理會它們。我偷偷地起床赤著腳佯裝下樓上廁所,坐在馬桶再看看四周沒拉下沖水繩便拐著上樓回房間,故意在房門上輕輕踢了一下。過了一陣子再來一次,大概三或四次,直至聽不到牙們在說話而止。在浴室自不然會碰見姐的牙刷,它慣於獨自背靠水杯仰望著發霉的天花。刷頭部分的毛越來越往外彎曲,看來姐之前跟它好像聊得不太順利。在馬桶上坐得太久雙腿會麻,有時候我會蓋住馬桶站了上去,扶著後窗窺探對屋浴室的現場。我不夠高把窗推盡,只能僅僅望見對面的後窗範圍。對屋室內忽然點上黃光,牆壁鋪滿了海藍色的天空,每片天空都飄浮著一束累贅的氣球。對室的蒸氣急速上升,抽氣扇因過熱而按不住向前奔跑,它扯來了水氣,更扯來了刺鼻的香味。瓷磚的氣球緩緩將兩個頭顱牽起,一個魚人正在用力啃咬一個男人的嘴。姐確是這樣冷靜地向我敍述的。
我分辨不了那是她的經歷,抑是嫲嫲的故事,到了現在我仍未遇見過。
我遇過嫲嫲在碼頭買來一個西瓜,於八月的每一日。她不但沒將西瓜剖開過來吃,反而讓它默默地伴在床邊。待至第二天,嫲嫲一起床就拿著珠串合十,重複唸著一段不是輕快的曲子,然後在門前向海的空地躬身焚香,挽起藤籃背著西瓜出了門。她整個人被壓著背骨猶如鍋中煮熟的蝦子,走得比平常較為緩慢,但是回家時背上的籃裏又成功地換上另一個西瓜。
八月的風時而吹得很大,嫲嫲吩咐父親的漁艇也要在繩樁多綑上幾個結。艇上依然放著當日去直木島時的圓筒和魚罟,暗板下的竈還堆了潮濕的柴。我還不肯定自己將來會否再到直木島一趟。母親抓住水喉如期地把艇涮洗過後,便帶上了我和姐走到阿姨的魚攤幫忙,這次卻有點匆忙。母親照常留在攤內從推車搬動魚箱,阿姨就領著我和姐走上狹長的樓梯到二樓的房子去。梯道兩側的牆都擠滿粗大的電線,從一戶鑽進另一戶,我們不難聽見別家門後的私語。阿姨的房子跟我們住的並不一樣,它只有二樓這一層,樓上已是另一家人的住所。阿姨替我們開了大門便跑回樓下看攤。廳中的掛牆懸著幾幅舊的人像照,有些人的外貌還跟阿姨頗為相似,額頭及顎骨都是屬於方寬的臉型。嫲嫲曾幾何時也給我們看過類似的黑白照片,那些人的頭都是很細的。照片下安置了長方形的魚缸,高度差不多有我的一半,而缸裏養了一尾游得好慢的大魚,姐高興的指著牠說是泰國鬥魚。她立即握起櫃上的鏡子,把它垂直地放在鬥魚的面前,讓牠不惜對著自身炫耀那如摺扇般攤開的橙紅尾鰭。我們逕自拉開鐵門走出陽台,再先將幾盆擋風的盆栽移走。從這裏可以眺見碼頭四周都泊滿無人的船。我們花了半天終於指出父親的艇,原來它比剛才看見的細小得多。不過自那天後,一般我們都不會長時間留在陽台,因為樓下常常湧進難耐的魚腥,而且很快我們已經把陽台的景都看膩。
姐突然從後將我的褲子脫去,這是她上星期才發明的遊戲。可能我們都把屋子遊遍了,無聊之際她想出幾個遊戲,脫褲子是其中的一個,亦是最差勁的一個。我退了幾步,馬上拉回褲子,一手扯著她的背心,瞬間便鬆開了手。姐又哼的笑了一聲。她總是這個遊戲的贏家,每次我把手伸了過去,就不敢再作任何行動。初時姐也有用手擋著我,或會退後幾步,後來看我只是扯住她的衣褲後,更不去閃避了。
屋前的大門敞開了,只穿上短衣的阿姨搔著凸出的肚皮打了個呵欠。我和姐立時回復平靜。阿姨先行上來是因為要給我們煮午飯。她伸手重重的搭向我們,姐忍不住喊了聲痛,她接著又捏了一下姐那渾厚的屁股。也許阿姨發現我們弄過她的泰國鬥魚。她脫掉淺灰色的鴨舌帽及腰包,一邊抓著頭上的短髮,一邊趕著我們出廳。她關上陽台的門抽起了煙,吐出霧時向樓下飆了句髒話,我感覺她那遍佈頸項的紅斑逐漸顯眼起來。事實上我並不熟悉阿姨,只是過年時見過了幾次,反而母親和姐應該比我見得更多。聽母親說她是父親以前出海到直木島時認識的。所以阿姨的紅斑有時會使我懷疑她是從島上的博物館中逃走出來的標本。在潮漲的時候,若姐去不了灘頭就會跑去找她。我想姐相信她很有可能得知一些行蹤,不論父親或者是魚人。然而回來時姐一如慨往沒告訴我她究竟知道了甚麼。當她換上短褲之後,我看到她那雙黝實的大腿發著一塊塊魚鱗似的瘀青,隨著時日越見越多。母親亦看見姐大腿上的瘀青,她認為那些都是姐在外面亂走亂跳才弄成的,我也是這樣覺得。
母親從阿姨手上陸續端來一碟煎煮好的桂花魚和五碗白飯,她用筷子夾掉魚身上的蔥,再將魚腹的皮肉使力綻開。我嘗了一口,是塊混和了醬油及薑辛的白肉,除了溫度以外,與母親平日煮的白凍魚肉沒太大差別。我不喜歡它。母親硬把魚尾屈斷夾起,拌着幾塊鬆脫出來的魚肉,一同放在其中一碗白飯上,然後擺在身邊的空位前。我已看慣母親這樣的做法,因為吃飯時嫲嫲也會做著同樣的事。母親叫姐多吃點菜,再下去她會肥得像豬一樣,可是姐仍然只顧夾著魚肉。最近姐的身體確實是起了些變化,她長高了點,同時肩膀似是橫向地擴展,連胸前也微微聚起贅肉。這些都不太要緊,相反姐替自己設計的新髮型我是最看不慣。她解釋這是為了吸引魚人。她昨晚待在浴室跟剪刀談了好久:
「你做得到的,只要不斷張口呼吸,其他事我處理就好了。」
「我絕對不會被你弄痛的,來吧,不用害怕。」
盥盤的周圍還殘餘沖洗不掉的碎髮。姐戴著不及耳和頸的短髮走出浴室的時候,我們所有人也只懂得向她盯著發呆。嫲嫲駭然把手中的葵扇盡力地丢在她身上,開始罵起上來。母親回過神隨手拿起衣架便不斷往姐的手臂附近打去。姐只是平淡的向她們微笑著,但入睡時仍然由於疼痛而哭了一會。那晚,牙們因事討論得十分熱烈,我也同意它們說姐兩邊的頭髮剪得不太對稱。
母親把菜夾到姐的碗內,姐吐出尖長的魚骨滿足的打了個嗝,擱下了碗。阿姨最後還是問了姐是否前世跟魚有仇。不是的,我知道姐只是純粹地不討厭魚而已。
「我很想念魚人。」姐伸進衫內按住自己漲痛的乳房,對著灘頭的石頭說。我對她這種說法不覺得奇怪。在母親不再煮魚以後,姐近日都少了走來灘頭。吃飯時我們都是吃著除魚之外的肉,當然還有豆類和菜。母親對我們說以後都不再煮魚,因為在砧板上切魚的聲音會打擾到嫲嫲休息。我們都知道這是母親的藉口,其實母親自己也不喜歡魚。母親如常地將盛了餸菜的碗,好好的放在她身旁的空位前。在那空位的隔壁又多了一個空位,是嫲嫲原本的座位。母親隨意夾了一些素菜便把碗拿進嫲嫲的房裏。她在裏面留了好久才出回飯廳。吃過飯後,母親疊好了碗碟就走進廚房。姐忽而拉著我走到嫲嫲的房裏。房內的情景依舊沒太大改變,床頭依然覆著長身的書法布帖,嫲嫲曾把帖上的字說過一遍,但現在我大都忘記了。衣櫃上還擺著父親的笠子,高高的盯著我們。我們往床上瞟了一眼,上面躺著一隻煮熟了的弓身蝦子,是唯一感到陌生的事物。她乾瘦的外皮緊緊裹住四肢,她的軀體動也不動硬得像蒸發了所有水氣的紀前化石。姐靠近床頭,向靜止的嫲嫲打了招呼。嫲嫲奮力地嘗試拉直壓壞了的背骨,儼如洩了氣的氣球逐一噴出單字,然後造成句子。我瞥見矮櫃上碗裏的飯還剩下很多,姐向我說這一切都是正常的。我把嫲嫲的碗拿了出廳後,與母親坐在沙發上合力剖開了一個沉實的西瓜。
母親終於把父親的漁艇賣走了。
姐抓起灘頭的石向前拋去,因它缺乏西瓜般的重量,在水面上未有如她所願而綻成巨大的水花。由於母親不再煮魚的關係,午飯時我也沒再見到姐的出現。她是去了阿姨的家吃飯,我猜想。我不想跟著姐去那個難耐的地方,甚至是灘頭,也漸漸不想再去。我入睡前對她的牙們說這是最後一次來灘頭,或是因為這個緣故,她頭一次扶著我來到了這裏。我走在她的前面,四處探索,這地方是有亂石,有寄居蟹住過的螺殼,但就沒有嫲嫲和姐曾經提及的窪,附近更加沒有魚人居住過的痕跡。我出奇地沒有感覺失望,心情反而輕鬆了起來。姐在身後拾起一塊更大的石,遞了給我。我勉力用雙手接了過來。
「不如我們再玩脫褲子遊戲。」姐還未把話說完,已迅速地脫去我的褲子。我扔下了石,立時伸手扯住她的衣領,打了她一巴掌。姐索性把背心脫掉,光著上身整個壓了過來,我望見她的肩上長出了五或六片魚鱗似的紅斑。她反扣了我的雙手,我聞到姐的腋下散出的汗臭。她坐在我的腿上,輕易地脫下了我左邊高一點的鞋子,跟著使力向海中擲去。那時候,我看見了水花、父親駛去島上的漁艇,以及正在漂浮的腫脹的黑色膠袋。姐站起了身,轉過頭向我展露出平淡的笑容。我喘著氣仰望太陽悄悄地攜著影子從她身後沉下,彷彿聽見有人在她背後哼著一段不是輕快的曲子。這曲子嫲嫲曾在房裏唸過。
我想我還是適合在直木島上居住。我忍住不去搔著那手臂上的紅斑,心裏這樣對著母親說。我兩次都很費力用肥皂擦遍了全身,但是洗澡後仍會聞到身上遺下了姐的汗臭。母親闔著眼緊握珠串固然沒有回答,只是哼著一段與嫲嫲舊時哼著的相同曲子。母親仍未察覺到平日在唸文的時候,姐會安靜地倒在她的懷中,安然入睡。姐的頭髮恰似水蛇般蠕動緩緩地向下生長,蓋住了耳朵,蓋住了頸項,最後是肩膀。地板上滾落了兩顆晶瑩圓潤的眼珠,我看見姐的眼窩內好像欠缺著甚麼。她肩上的紅斑也暫時沒如夏末的魚群急速地繁衍至全身。我知道那是因為夜晚的月亮不是很圓。我在裝睡的時候,一尾活了過來的桂花魚曾於眼縫間悠然游走。我睜開了眼側過身去,隱約見到河流傾瀉滑過姐那黝黑的身體,肩上的紅斑逐漸像疫病往外擴散,她將自己的臉扭曲成魚的表情,跳出水面勉強地呼吸,重新成為一個接近正常的人。
我盯著床上一尾快要脫水的魚本能地覺得好餓。
一年後的八月,母親帶著我乘上了別人的船正式搬到直木島。船上堆着約略四個偌大的膠箱,箱內有摺疊好的衣物及日用品,嫲嫲和父親就被夾在陳舊的棉被間靜默地躺著。姐沒有如期地跟隨上船,據說有晚她與村外的一個女人在凌晨時分離家出走。看來這事是真的。沒了姐的牙,那晚我睡得非常安穩。船駛近了灘頭,我想我以後不會再回到這裏,也不再相信魚人的存在。姐離家之後,母親和我都沒見過阿姨。我們有時經過了碼頭的集市,阿姨的魚攤好像已經易了手,而上面的陽台也被掩上藍白色的幕。我立在船頭拿著裝上銀白尾鰭的果汁瓶。縱使姐不在家,我每日都細心地將它拭抹乾淨,瓶上因而沒有黏上厚重的灰塵。我對它哼著一段輕快的曲子,太陽漸漸在它背後再次升起,水面上不停地湧來破碎的光。我不記得姐的手指有順利地進入過我的身體。我鬆開瓶上的手,尾鰭隨著大海忽倏浮游。我蹲了下來,別過頭用手擋下水上反射出的刺眼的光。我突然迎接了初潮。
Inspired by ptcr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