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註冊,結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讓你輕鬆玩轉社區。
您需要 登錄 才可以下載或查看,沒有帳號?註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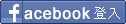
x
本帖最後由 Lazarus 於 2014-11-6 14:27 編輯
2 他是在大學的社會工作系經過3 年全時間訓練後,隨即受聘於那社區服務中心、去實踐他做一個社工的理想。他很喜歡這門助人自助的專業;出道後一切都很順利,所以工作5 年後,他再用兩年以兼讀的方式取得社會工作碩士學位,也在工作上增多了行政管理的角色。簡言之,事業是按著他預期的軌跡暢順地滑行;一切都近乎理所當然的,一直至步入第10年,在今年年初,那事情是那麼突如其來地發生、那麼令他措手不及── 那天早上10時左右,他在辦公室接到她的電話。她這個家庭對於他是那麼的熟悉,是他出道不久即開始介入幫助:她的丈夫怎樣戒賭甚至積極地去幫助人;她的女兒怎樣由反叛少年變成勤奮的學生;她家庭的經濟如何清除了債項以致稍有餘裕……這家庭各成員彷彿就是他的家人。 她語帶慌張地說:「阿邦入了醫院。今朝吃完早餐,胃口還好好的,突然說胸口覺得很不舒服,就進了醫院急症,現留院觀察。」 「他現在狀況如何?神志清醒嗎?」 「他清醒的,剛才要過床,他還說自己可以,不需護士幫助。當然護士不會讓他自己來。」 「那就不要太擔心,未必有什麼大礙的。入了醫院就好了,醫生會小心照顧他的。我現在也去醫院找你。放心吧!」他以和緩的聲線嘗試助她鎮定下來。他實在也估量應不是什麼大問題,可能只是因他過度疲勞導致;當做完幾個檢查,打個點滴,稍事休息,應今天稍後即可離開醫院,最多是再住一兩天吧。 他迅速離開辦公室乘車往醫院,但心底並不怎樣焦急,在車上讀著常帶在皮包內的書,腦筋不太集中,只是天馬行空地想著各樣的事情。 踏進病房旁邊、一個供病人的親友休息等候的房間,看見了她及她女兒相擁著失聲地哭、扭曲著的面孔展現出痛苦和驚恐,他意識到有一股黑暗的破壞力量充斥這房間。他感覺耳內有一條無形的線瀕將斷掉,就像電話接線快斷未斷發出「沙沙沙」的不祥聲音;他不知何解這刻自覺身體變成一個透明的外殼,「他」退在裡面望著外間發生的事情,像隔著一個真空玻璃罩似的,原本嘈雜的聲音消減了一半的聲量。而周圍的一切像一張水彩畫掉在水中,顏彩正在慢慢溶掉。 原來在半小時前,那婦人的丈夫病情急轉直下,有如坐過山車從最高點突然急墜,甚至靈魂也被甩出身後,分別是只有急下而再沒有回上;或許,那更像一隻鳥兒,在天空飛翔時突然中箭,只能順著地心吸力不斷加速地往地面直墮。 那男人現正由一組醫護人員試盡餘力在搶救中。而他,一踏進這裡,突然身陷這情勢,沒找到1 秒的餘裕讓他去思索,究竟箇中有什麼意義、或底蘊、或奧秘。他只能緊貼著情勢、逡巡往返於病房與等候房之間──一邊查看著醫護人員的施救有否突破進展,另一邊不停去安慰正焦灼等待消息的家人。他已怎樣也無法記起當時他向她們說了些什麼話,抑或他也失措至無言? 當一切醫生的努力、家人的哀盼都不能逆轉情勢,他所能做的,是攙扶著那人的妻子的臂膀,去觀看那口鼻滲流著血的遺容──他們都知道,那人看似是一動也不動地停留在床上,但「他」已無從挽留、一去不返地離赴他方。 他那時不自覺地翹起他的下頷,環視著病房的天花板,彷彿看到一隻候鳥正在振翅高飛、動身前往那飄遠的另一方。他在想:「他原先知道自己是候鳥,而不是留鳥嗎?」 † 「抽乾了水份,扣減了靈魂,一個『人』的重量,原來是那麼的輕、那麼的虛緲。」他在公車上,回想著那兩秒的情狀──他剛才陪同那過世的人的妻子,去殯儀館取回骨灰;他從那裡的職員將那一小袋東西接過,然後再交予她,就是那中間短短的兩秒過程──但他的思緒就定格了在這兩秒,無法掙開。 那是不足他平日買一袋咖啡粉的1/ 5重量。 公車徐緩寸進,努力突圍一排又一排夾迫的三合土牆,焦躁得就像草苗極待破土而出。甫衝上快速公路,視界豁然開朗,他自然地翹起下頷,瞥見遠遠的天空,有一頭鷹,正在一所精神病院上盤旋打轉,像在搜尋獵物。他曾聽人說過,麻鷹是不會真的捕食活小雞的。霎時,腦中浮起未經沉澱的聯想:牠大概認為那裡是裝載著生不如死的人的地方罷,可惡! 轉眼看另一邊窗外,沿著修直了的海岸線,排列整齊的貨櫃起落架,猶如魯鈍、未開化的大巨人,正向著發紅的落日,或舉手、或俯身膜拜,似是祈福著什麼、更像乞憐些什麼。 他可以說是一個只見森林、不看樹木的人;許多時對於生活周邊的事情,他就只安於掌握其概括大略。所以,他從沒有積極將公制的概念兌換在實用的領域;高矮肥瘦,在腦中始終用「呎」「吋」、用「磅」「安士」,才能模擬出空間長短、或體會其質量輕重。他自己是5 呎9吋高,重145 磅;而那男人的高度與他相約,但略較肥胖,所以猜他應有160磅。但現今卻剩得幾安士的輕。 他當然也沒有動機去根查那些巨人的吞吐量,模糊的印象是:「第一」,香港近年已無法保住,先後被新加坡及上海趕過了。當然,他也不會嚴肅地去考究、剛才那飛禽的確切品種。他曾參加過一些「觀鳥」的講習班和旅行團,導師雖然對種種雀鳥作出精細的解說,但他總沒能記得住的;殘存的大體是,有歸類為「留鳥」的、及「候鳥」的。候鳥又有分由北半球南來香港避寒的,而另一些則嫌這裡仍然太冷,由香港遷往更南的地方渡冬去。簡言之,同一地方,總可以被看為天堂或地獄的;同一件事,也可有截然不同的兩面。 公車由快速公路切入了如纏結領帶般的天橋,又如闖進了充滿無形引力的軌道,一直被牽引至驟然的黑暗、彷彿吞噬一切的黑洞內。不過,所謂「黑暗」是相對而言的;「黑洞」也既非是一個無奈的終局,更絕不是我們有時會歡迎的、事理簡單的結束。只是,車廂裡,並沒有引發起絲毫半點的躁動──驚駭的或喝采的──大概因為這段路程,完全是在他們預期當中罷,絕不似他不久前所經歷的! 隧道內調柔了的燈光,叫那些已睡的、沉溺得越發不能自拔;勉力保持清醒的,亦因由正前方不斷激射而來的光束,上下左右的飛越身旁,也開始著了圈套、陷入目眩迷惑之境地。只有他眼仍睜開,視線凝定在隧道遠遠的盡頭,但同時亦是時間長廊的背後──那個家庭過去將近10年如何拚盡一口氣地掙扎、努力,他參予其中的數不盡的片段,也快速地在他腦際飛閃而過…… 但教他最無法忘記、叫他的心猛烈搖撼的,是當那對妻女弄清醫生猶如法官的終審判決時,她們是怎樣的徹底崩潰了,那尖刺的哀呼聲比刮弄玻璃表面的刺耳聲,更強烈百倍地刺激著人的神經,叫他久久不能平伏。 一陣顛簸,公車此刻猶像厭倦了家的男人,只求盡快逃離隧道;又如苦戀的燈蛾,不帶半點猶豫,向光亮處猛撲而出──都不管擁抱上的是救贖的光明、或只是毀滅的火燄。 不過,一山之隔,景物儼如舞台上的佈景板,可以完全不相銜接的遽然變換:四五重山像公式的行畫般、由黛綠至粉藍向遠遠的背景開展去,其間環抱著一片尚算廣闊的平原。倨傲侮慢的高廈消失了,變成的是矮與周遭林木齊平,不帶氣焰、不假虛飾的村屋小樓房,還有整齊地蒔著花卉、種著菜蔬的農田。 他內心原本井然的秩序,不知在哪裡有些螺絲釘開始鬆動了──縱然她沒打算追究,但他沒法原諒自己竟然對她做出那樣的事情──他彷彿感到裡面有一座像高塔的物體在左右擺動,陣陣的暈眩感直令他有想吐的反應。 窗外,夜幕不知從哪一刻開始暗暗被啟動,徐徐地向地平垂下。對某些人那感覺可像是舞台上劇終時、帶著無限依戀、不捨告別的幔幕;對另一些人,那或許仿似是上天給予覆蓋蔽體的衣衫被褥,體恤地簇擁著已滿載落寞困頓、仍在歸家路上的人。 但他已知自己回不去了。對於他,黑暗的力量已壓倒性的如推倒第一塊骨牌般、開啟了傾覆的程序,倒塌已是勢不可當! 那意想不到的事既已出現,唯一的選擇就是離開。 他輕吁一口氣,不自覺地又翹起他的下頷,與天際間透著蕭瑟的星眸打了個照面,但他迅即垂低了頭、闔上了雙眼,試圖將自己埋藏在夜色裡、隱沒於周圍已睡得深沉的乘客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