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註冊,結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讓你輕鬆玩轉社區。
您需要 登錄 才可以下載或查看,沒有帳號?註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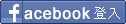
x
本帖最後由 心雪 於 2010-2-4 23:02 編輯

編者話:為觸感命名 葉輝
1.
那是2003 年5月吧,其時與關夢南共事,在咖啡或茶之間忽發奇想——《秋螢》可以復活嗎?阿關說,事在人為。幾天後再在茶水檔碰頭,他已做好了一個「復活樣本」,電腦排版,影印,人手釘裝,那就是半手工業時期的《秋螢》胚胎,簡樸而包容豐沛的想像,粗糙而不失原創的觸感,那就很好,那就正好應合了一句老話:萬物的想像先於一物的製作。
《秋螢》誕生於1969 年, 40歲了;這份詩刊經歷了油印、鉛印、海報與明信片等不同時期,它的命運一如歷來前赴後繼的詩刊,旋生旋滅,旋滅旋生,每一次想像嘗試失敗,便休養生息一段時日,等待另一次想像回歸。半手工業時期的《秋螢》輕裝上路,限量發行,生命力竟比初始的想像頑強得多,三年又三年,不覺已完成了兩個「三年計劃」,如今由一班年輕人接力製作,抖擻精神,邁向另一個「三年計劃」了。
柴九哥說:人生有幾多個十年?我想跟阿關說:十年太久,六年已夠本夠利了,往後每出一期,都是賺來的。我已編了一段時日,下期起,由阿關接手。
2.
《秋螢》的製作既是半手工業,簡樸而包容豐沛的想像,粗糙而不失原創的觸感,這一期的詩倒也剛巧有一個「潛主題」,簡言之,就是「想像」遇上了「觸感」。我首先想起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論靈魂》(On the Soul),想起他論說的疑難:「觸感」(touch)既然是所有動物感官最原始的形式,那麼,「觸感」是一種感覺還是多種感覺?「觸感」為甚麼沒有專一的對象和客體?
最近為不信(盧勁馳)的詩集《後遺》撰序,對詩集所突顯的「失明」與「觸感」多所想像,要是用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話語來應對亞里斯多德的疑難,也許便有此暫時的推論:「觸感」僅僅只是一種生命的潛能,而不是現實的,失明者或失焦者要是不與他者接觸,「觸感」可能就變得甚麼都不是。這「觸感」永遠跟「他者」互相糾結交纏,絕對的「他異性」(alterity)由是被啟動了——總是渴望「觸及」,那就意味著必須「觸及那不可觸及的」(touching the untouchable)。
這一期的「卷首詩」是雨希的《當我說愛》,引詩為狄堇蓀(Emily Dickinson)的集句——集句正是一種與閱讀的對話,也是一種互動的創作:「我不能和你一起生活�因為我不能等待死亡�說出全部真相」,那彷彿為愛的觸感、想像與消亡拉開序幕,嘗試命名,時間的擬聲交織夫婦暗室按摩的影像,這是肌膚之親,「也是阻隔」,「總差一步�觸感裡永恆延誤」,兩人「偶爾瞥一眼電視裡的遊行�雪白床單外的憂患」,人是眼前人,感覺何以漸行漸遠?那大概就是「觸感」與「想像」的無限延伸,在如此或如彼的流光裡,「想像」有多遙遠,「觸感」便有多遙遠,那怕只是「總差一步」。
「如果愛情是一種交換」在時光的流逝裡只是被理解為「交換體溫、體液�交換空間裡的佔有」,最親近的觸碰可能就變成了茫茫人世裡最遙遠的不可觸及,「那就稱為逝去�渴望的逝去�觸碰的逝去」,那是最近也是最遠的逝去,一種或可稱之為愛情的「觸感玄學」(haptocentric metaphysics),一種愛慾交纏的「他異觸發」(hetero-affection),倒使我想起,在《後遺》的序中,我說有一回與梁文道對談「愛情書寫」,不知是誰擬定了這樣的講題:「當愛情衰亡,書寫才剛開始」,一看到這十一個字就不禁心神微顫,便想:那一定是「觸感」,總是渴望「觸及」,那就意味著必須觸及那不可觸及的,或如捷克電影《親密閃光》最後的凝鏡:一杯凝結得太稠的蛋酒,都仰首,都渴求一飲而盡,可是舌頭老觸不到那凝止了的欲望,you are in the middle of longing。
3.
「11 種觸感」照例並不光光是巧立名目,陳麗娟說「我以錯誤的公式計算距離」,在消逝的時候,形態各異的貓(或母雞)就成了「能觸」或「所觸」的「矛盾語法」,或是何倩彤以各種玄思試圖觸之摸之的「時差」,或是江濤詩中的「手機」探詢:「經過的路,都是無路,永夜相隨」,或是趙婉慧在旅途上的感悟的「最終都是一個人走又不是一個人走」;對陳滅來說,那是咳嗽所發出的「觸感」:「它總擾亂自己的語言�它若重整只因情感仍尋找根源」;對蔡炎培來說,或是「觸」者,「燭」也,「燭光不瞬幽靈舌至」,來日方長嘛,「你的餘生我接受�聲音咽了」。「11種觸感」每一首都幾乎是「編輯精選」,可是最終還是選了西草的《白晝的史詩》和《連花開的聲音都沒有》。
西草的兩首詩未必優於「11種觸感」的個別作品,但這位作者的進步幅度大得驚人,教我感到近乎眼前一亮,《白晝的史詩》三段都以「我是光明正大的太陽」開首,都以「事件發生在白晝」收結,這太陽在三段裡分別看到了一個農夫,一個工人,一個寬帶推銷員,前兩段還有重複的句子——他喊:「慘啦慘啦!……」我想:「怎麼慘叫聲都一樣?」最後一段說到寬帶推銷員「被第n個路人拒絕」�他說:「沒關係。太感謝你的時間了!」我想:「怎麼慘叫聲不一樣了?」由兩個「都一樣」到最後一個「不一樣」,著一「不」字,慘況便有了厚度,那就是「繁複的簡潔」,在繁簡的辯證裡見出意義的差異。
喜歡《連花開的聲音都沒有》的第一段:「交通燈知道�欄杆知道�郵筒知道�城市的衣服是安安靜靜的�連花開的聲音都沒有」,那是透明的「廢名風格」;喜歡末段的說的「冬季在流浪�塵在流浪�流浪狗在流浪�廣播在流浪」,以及流動裡的簡靜:「城市中的人�安守本份�安安靜靜地做人�在安安靜靜的�港口城巿」,簡潔而不失細緻的感覺,永遠是詩最可貴的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