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註冊,結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讓你輕鬆玩轉社區。
您需要 登錄 才可以下載或查看,沒有帳號?註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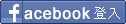
x
本帖最後由 心雪 於 2009-10-21 01:52 編輯
可以說,這是我的近作。登在最新一期的《小說風》。
破碎的床景
當我離開床,便失去了所有的力量。
明走出了房間,牽引著,這種牽引不是來自她的本身,是來自她背後的一個他,一個連名字也不知道的他。
只要我一踏出了房門,便成為一隻甲蟲,四腳朝天,呼天搶地也得不到回應的生物。而她偏偏是一個從來不怕任何昆蟲的女人。最後,我變成了她的影子,就算有光的地方,也不過是依附著她的足下。
在床上,全不同了。我可以滿足她。她的每一刻呼吸都為我而伸延,在我的指間緩緩遊走,她閉上眼睛,咀唇半張,告訴我一切,包括謊言,謊言背後的善意,善意背後的欲望。我自願盲目,只管滿足她。
翠問我:你真的愛明嗎?她選擇了一個不適當的地點。麥當奴。有一次,在深圳的麥當奴。右邊桌子一個年輕的母親,把手抱的小孩的褲子拉下,當眾在座位前撤尿,完事後便走開了,仿佛什麽事情也沒有發生過。我望著地板上那灘尿水,良久說不出話來。麥當奴,永遠是一個不適當的地點。我再望翠一眼,真想這麽對她說,愛情就是這樣,撤尿,其實,與㺃沒有分別,到處撤尿,完事後便跑開了。
翠當然記得,在床上,我也說過我愛她,是多麽愛她。她那張咀一直給我無比的快樂。傷口式的抽搐。抽搐就是一種無比快樂,尤其出現了極致的抖顫,蜂鳥拍擊翅膀,我真以為從此我會癱瘓,再不能起床。有一晚,更是電閃雷擊,我們一起大叫起來。My my, dive and die. Oh, god, die with me.從她唇齒間吐出的,都是愛的津涎。聲籟是靠動作的細節去和應,一碰一撞之間,或一高一低之間,或左或右之間......說來說去,就像寫詩詞一樣,平或仄,或平仄或仄平。我常在女人身上玩耍類似古人射覆之樂......管輅曾以佈卦之術,依照所得的卦象尋找收藏的事物︰高嶽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她的確是朱身之鳥,鳴不失晨,使我吟出了柳永的《曲玉管》:每登山臨水,惹起平生心事,一場消黯,永日無言,卻下層樓………
我不明白為什麽要跟蹤明。也許完全是這種心理的作祟:還有人在床上比我更滿足她嗎?只是這麽想吧了。我無能為力。完全失敗。一個轉彎,明便消失了。我走到街道的盡頭,找尋棲身之所。我的酒吧。我熟悉的酒吧。但今晚我熟悉的酒保阿尊放假了。面前是一個女的。她叫蘇菲亞,說她認得我,一聲as usual? 一瓶熟悉的啤酒很快便擺在眼前。傳來並不熟悉的歌聲:
Underneath Your Clothes
There's an endless story
There's the man I chose
There's my territory
And all the things I deserve
For being such a good girl honey
Underneath Your Clothes
衣服下面,伸延著無盡的故事......
阿尊不在,我的確有點失落感。許多時候,阿尊是我的鏡像,在他面前,我可以看到昨日的自己,拾回自己,然後嘲笑今天的自己,輕視自己。
Underneath Your Clothes………衣服下面,我看到蘇菲亞的衣服下面,一件印上 FUCK OR HATE的 低胸 T 恤的下面,乳溝的深處。Johnny, my brother. 悅耳而音準的英語。我馬上想起Eve,只有一夜情的Eve。
那晚她是半醉, 我是乘虛而入,so what? 我與她從波特萊爾開始,而奇奇怪怪地,在她的馬龍白蘭度和我的歌蒂亞嘉汀娜而告終。也是一件低胸的 T 恤,下面什麽也沒有,隨著音樂,雙乳如波如浪,也如火,點燃了性交完畢便溜跑的老故事。
我和她必然有一個共通點,否則我們不會這麽快便爬上了床。我們的共通點就是:我們都覺得彼此並不實在,而活在虛擬之中。她在丹麥住了好幾年。I know what ice is and how the fire can do something about it.她比喻人生如碎冰,若不爭取時間咀嚼,它便變成水的了。我問,咀嚼是重要麽?她的唇舌微動,彎下腰,在我那發燙的陽具上滑吻一下,涼快襲來,舌尖卷起,我看到來自她酒杯內的冰塊,她湊過來,我聽到冰山劈開,刹那間,冰如流星灑落我的口中。我明白了,她說的,經咀嚼後,冰才有氣味。她私處的氣味,我陽具的氣味。
「液態是沒有意思的,它必須凝結成固態,最後化成氣態,才是高潮所在。不是味道,是氣味。」就是這麽奇異,一夜的氣味,留存在我的體內,經年不散。而且,每次都會拿它比較不同的層次,不同的線條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形狀;每一次在床上,我便靠著這些材料,建構我的情欲工程。
我讀過一個故事。一個男子追求身家千萬的女人,他比喻自己,從一個游泳池遊到另一個游泳池,每天朝早,每個夜晚,他不眠不休,費盡氣力,直至他抓住了她那在水中撥動的足踝。而我從一張床爬到另一張床,朝早如此,晚上也如此,可惜我無法跟他相比,他的主角是身家千萬的女人,他還可以抓住她的足踝,而我,看不到終點,偶一擡頭,前邊是無盡的房,無盡的床,無盡的女體.......僅此而已。
看來,是我的堅持,所以我跟蹤著明。
女詩人Plath 把頭埋在煤氣爐內,我是理解得到的。翠的初戀男友與她吃過早餐,一言不發走出陽台,便縱身下跳,我也明白的。我不明白的是她嫁給一個不知公義為何物的議員。那晚,在電視機上看回歸日升旗儀式重播,她丈夫站在其他官員之中,張大咀唱國歌,全情投入:起來。起來。起來………我在床上,也全情投入,起來。起來。在翠的雙腿間起來。在她咀巴裏面起來。她從來坦白,她的一切,毫無隱瞞。翠是一個絕頂聰明的女人,她冷靜地觀察著,一旦看穿我,也從不揭發。她知道,我再不會是上街遊行那種人,我已經死了,她想要的是還有一息尚存的部分,到最後,她便親手把我整個人殺掉。
翠不停地問,你真的愛明嗎?
明轉入走廊,我尾隨著。她終於在一度房門停下來。房門開了。她進入。我連忙趨前。房門原來沒有上鎖的。輕輕推開。大大的客廳。起初沒有動靜。不久,裏面傳來了浴室的水聲。一個男子在沖身。我認出他,他是明的辦公室IT部門主管Tom。電視機亮著,但沒有聲音。黑白的錄像。五十年代的香港街道。房內什麽人也沒有。
IT部門主管Tom轉入走廊,我尾隨著。他終於在一度度房門停下。房門打開了。他進入。我連忙趨前。房門原來沒有上鎖的。輕輕推開。大大的客廳。起初沒有動靜。不久,裏面傳來了浴室的水聲。一個女子在沖身。看清楚,她不是別人,她是明。電視機亮著,但沒有聲音。黑白的錄像。五十年代的香港街道。房內沒有其他人。
男人在床上滿足一個女人,是與愛情無關的。英文的making love, 最貼切不過。愛情,是製造出來的。製造出來,就不是自然發生的了。威尼斯酒店,不是小令,我不會懷念威尼斯酒店的一夜。小令比翠還開放。鬼節夜我在蘭桂芳碰上她,她身邊還有三四個男人,個個的年紀都比她大。她最後選中了我,我不清楚是什麽原因,我也不想知道,我緊緊抱著她不放,是她醉,還是我醉,也記不起來了。她大聲地說,帶我飛吧。還說出了,不像她年紀會說出的話來:「天使有翼才會飛。魔鬼根本不想飛。但人類,沒有翼也會飛,所以上帝發脾氣了。」在床上,有一次,她便說,「你把我從上帝的手上拉了出來,謝謝你。」小令比任何成熟的女人都熱情。她完全釋放自己。她是一陣狂風,把我吹倒。與其說我帶她飛,不如說,她就是我的情欲翅膀。我於是對翠說,「就是情欲翅膀,不是別的,難道你相信我會愛上了小令才與她上床嗎?」她問:「小令是誰?」我簡單地答:「一個十七歲的基督徒。」
再過幾天,在我的熟悉的酒吧內,目擊小令與一個中年洋漢無比親熱,她穿得非常惹火,跳舞時高跟鞋的節拍,更加強了她小腿的信仰,飛的信仰。那刻,我才發現,原來人類不是沒有翅膀,而是長在足踝後面吧了。我熟悉她的胴體,當然同時熟悉她的翅膀。真想知道,她的母親是一個那樣的女人?
我問酒保阿尊她是否常客。他搖頭,他再搖頭,這麽說,「如果我是他的老爹,就頭痛了。 」我只能聳聳肩,不置可否,稍後,問他,「你溝女時也這麽想?」他狡黠地笑一下,說,「頭痛不是我。」我不想小令看到我也在酒吧,雖然我更想小令此刻抱的是我。電話響,不是明,不是翠,當然不會是小令,是李立。
每一次與李立一起時,總是滂沱大雨。下著下著下著。天空壓在頭上,烏雲在移動,我的頭髮與烏雲一起移動。我與李立的關係十二分矛盾。跟他見面傾談,過程中無法平靜下來, 快樂與鬱結集結在一起;想說很多話,又力不從心。他的實體,很遠,也很近。我分不出他是一個學者,還是活動家,或兩者都是。說他是一個頗有原則的人,卻是錯不到那裏去的。他愛談國家興亡,知識份子的進退等等問題。可是,這些東西,對於今天的我,只不過是一件件死物吧了。談到詩的時候,雙方的距離仍隔著一塊玻璃,幸好還可以看到對方。我許久許久沒有寫詩了,也快自決還是不寫會好一些。李立半嘲笑地說。「你的詩是為討好女人而寫的。」這算是瞭解我嗎?不算。詩、女人、我三者這種超文本式的關係是非常微妙,複雜的,也隨著時間變化。他不會明白的,他也知道,在其他問題上,我們根本習慣隔著同一塊玻璃。有一次,他似乎很認真的問我,「沒有女人的時候,你會怎樣?」我還未準備回答,他接著說,「我真不相信,沒有女人時,你會停止呼吸。」好幾次,我回避與女人有關的問題。只有一次,我反擊他,「你太忙了,忙到只得用不同的方法進行自慰吧。」他若不是有性別的傾向,就可能是一個性無能者。電視熒幕常見到他,上街示威,揮動標語。接受訪問時,氣定神閑裏面揚起熊熊火光。可是我看到的是不安,看到的是恐懼。我沒有告訴他,當書架上的書倒下來的一刻起,便決定再不相信文字了。我也停止解構我與李立的共存命題。外邊滂沱大雨,我沒有帶雨具,仍想離開。我想在雨中消失。事實上,他已轉身,不理會我。如果他遞給我雨傘,我可能留下來。一個眼神,我便留下來。常常到最後,還是同意碰杯。什麽酒都喝。我不抽煙,也陪他抽煙。大家已無話可說,也不互望。各有各做夢。只是等待。等待醉倒。醉倒了就等待清醒。清醒後,又等待再次喝得爛醉。我終不能忍受下去,不能忍受他不停翻書時的神情,以及書頁上文字交戰的聲音。我開始嘔吐。滂沱大雨。下著下著。大雨滂沱。
我陷落了。明的肉體命令我,還是她肉體內的另一些東西呢?她的每一個部位,都遺留著一些殘漬,茶壺裏面那種,而不想清洗掉。她的眉眼,令我想到烏爾芙;她的香肩必然是納波哥夫談論過;她那憂鬱的咀角,令我馬上記起年輕時的莎崗;她的乳頭,出奇地從馬蒂斯與達利之間游離;她的陰戶啊,是亨利米勒寫上十多萬字贊美過的。臀與腿,流水行雲,咬緊我,只要勁抽一下,水流成雲,雲流如水。歷史教科書告訴我,文明的誕生必與河流發生密切的關係。魚的躍動。在我的指間。抓住的高潮。她的腰肢輕擺,魚兒隨河水流去。
原來是我錯,離開床不是我,而是她,她一離開了床,我便失去了所有的力量。我必須抓住她的足踝。她的每一組小動作,都吱吱作響,她是蛇,但她叫著,「我是貓,我是你的貓,你看不見我頭上的一對耳朵麽?」喵……貓的肉球在我的身上愛撫。我完全失控。你愛我嗎?我愛你。你舒服嗎?好舒服。我的根壓貼你的心啊。壓緊些啊壓緊些啊。你你你你……我我我我……只有在這些分秒,我才可以從心所欲。你全身的機械都是我親手製造的我是你的主人我是你的主人。我只想佔有。每一寸肌膚的觸感令我作身血液流竄。她似乎已察覺到一些什麽,「別開玩笑了。你是知道的,紫微命盤,你是貪狼守命,而我也是。我們只會出外不停狩獵,不會關在房內死抱不放的。」當她離開這張床,跳上別人的床的時候,我會發瘋的。我對她說。她呵呵大笑。你不會的你不會的。她略一轉身,就是另一個時空,鏡花水月。我的確陷落了,完全陷落了。原來,原來啊,她才是我的主人。
911那天,兩座大樓都可以倒下,還有其他的事更加重要嗎?不是沒有,911那天,明的電話,說有急事,要見我。打開門,我嚇了一跳,她憔悴了,前額受了傷,繃布上還有血跡。正想問個原委,她便開口了,「你不必浪費時間跟蹤我了,你想知道我常見的男人是誰,對嗎?」她拿出一張相片,二人合照。我只瞄一下,馬上觸電。相片中的男子不就是李立嗎?我極力保持冷靜。「這個男人是我的前夫,三年前已與他離異了,但最近他突然想舊情復熾,死纏住我不放。他以我的女兒作為威脅。」遞過來另一張相片,就是她與女兒,站在沙灘上。一個更大的浪撞擊我的胸口,相片中兩個誘人的胴體,我都那麽熟悉,我都愛撫過,明身邊的女孩,不是別人,正是小令。我禁不住說,「她真是你親生的女兒?」「真怪了,我有理由要騙你嗎?」我不想露出馬腳,連忙說,「我只覺得她完全不像你。」她想說什麽,我急急地接上,「為何你會受傷?」她歎了一口氣,「前天,我與阿立坐的士,中途遇上了車禍,他比我傷得重許多,現還在醫院。這宗五車連環相撞的新聞,你也會在電視新聞看到吧。反正你遲早會發現,不如早點告訴你。所以今天我來了。」在什麽情況下,我才能讓她相信我不知道李立是她的前夫,更不知道小令是她的親生女兒。但此刻,我關心的是李立。「他受傷很重?」她點首,「他仍未醒過來。」突然,她流出淚來,我以為她是為李立而哀傷,正想安慰她,但她投入我懷中,「你知道嗎?自這次意外後,覺得生命無常,我,我不想失去你。」我不是想全占有她麽?真荒謬,現在還想嗎?可憐的貪狼。
第二天,我收到了一封信。我認出是李立的字跡。明顯是意外前寄給我的。信在書桌上,我沒有拆開,應該說我不能拆開罪的零件。
當我摟著翠,才明白到自由是那麽重要。翠總是與我一起欣賞床上的流動風景,破破碎碎的,但仍是風景啊。「你明白嗎?我問你是否真的愛明,完全不是妒忌,只想把你從懸崖拉上來。愛是你頭上的猛烈的太陽,你追上前只會枯渴而死。」我終於第一次說出我多年來從未說出於口的心底話,「我不喜歡下墜的感覺,年來不斷下墜,不外為了等待可以飛升的日子。但,近來,我的恐懼來了。你比喻我站在懸崖,其實,我早已跳了下去。」翠不說話,微微張開長長的玉腿,展露她那毛黑得神秘的陰戶,陰唇要說話,不是語言,是最原始的天籟。那天母親也曾張開了腿,我誕生了。此時此刻,母親仿佛重現在我眼前,我對她說,「媽,是你帶我來到這個世界,應是我回頭返回你的時候了,你的子宮才是我此生欲望之源。媽,我要抱抱你。」我盡全力挻進過去,魚的躍動,逆流而上的魚,非返回産卵地不可之魚。翠嘷叫,我也嘷叫,赤赤裸裸的,欲望的嘷叫。
我目擊自己離開了床,破碎風景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