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註冊,結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讓你輕鬆玩轉社區。
您需要 登錄 才可以下載或查看,沒有帳號?註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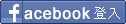
x
本帖最後由 wednesday 於 2016-12-2 09:32 編輯
牆的另一邊
黃稠的小米粥從她合不攏的嘴巴一次又一次的流出來,喂她吃早餐的女職員一次又一次的用那銀色小茶匙把流出來的粥翻掏進她的嘴裏,同時用毛巾拭去流到落她下巴的水份。女職員的臉像嵌著鋼板般的僵硬和冰冷,五官少有展露出它們擁有活的功能,也甚少眨動眼睛;連把稠粥翻掏回她嘴巴裏的動作,也充滿規律的機械性。 小米粥繼續在她的嘴巴間進出,多少因為她身體的飢餓本能,被食道蠕動運送到胃裏進行消化。 銀色茶匙再接進粥碗裏,輕敲了一下碗邊,掏出新的一茶匙粥,又再往她的嘴巴伸進去。 其他人也正在被喂食早餐,而負責喂餐工作的職員也同樣擁有著嵌著鋼板般僵硬的臉,以機械性的動作運行著。 她的眼睛一直看向隔離床的女人。 隔離床的女人在昨夜裏一直發出嗚嗚的低吟,彷彿喉嚨被掐住了,用盡力氣去呼氣,用盡力氣去吸氣,用盡力氣去呼氣,用盡力氣去吸氣……女人的床邊燈被巡房的護理員開著,燈光照亮了女人瞪著大大的眼睛。眼睛瞪得大大的,還要瞪得更大,更大,那裏像兩隻閘門,困迫住了體內翻動著,踢跑著,一隻焦躁不安,要衝出來的獸類動物。一群人隨即匆匆忙忙跑進房間。他們圍著女人的床,又匆匆忙忙的做著一些事情。拆開醫療用品的聲音。醫療儀器開啟的聲音。人們低語的聲音。漸漸聽不到嗚嗚的低吟。 現在女人的鼻腔深插著粗幼不一的喉管,被自動灌輸著氧氣,手上也插著喉管,打著含藥物和營養的點滴。喉管為女人的身體灌輸著物質,那些物質令女人的身體可以繼續維持運作,使女人的生命延續下去,但也呈現出一個鮮明的印象----那些喉管正在無聲地吸導出女人的生命。女人的眼神空洞,靜靜的流出淚水。 早餐時間完畢,護理員把她抱上輪椅,為她蓋好毛氈,然後按排她到療養院的四樓露台。 四樓的露台已經陸遂坐滿了人。每個人都被按排坐在他們所被編排好的位置,向著露台外的天空坐著。 每當天氣晴朗的日子,療養院的職員就會安排他們到四樓的露台,曬著早間的太陽,認為那樣會對他們的健康有良好的益處。她被安排的位置在露台的側位,剛好面對著一面牆。太陽常曬下金色的一角,落在她的腳上,像一隻三角形的碟子。坐在那位置的,還有一個頭髮差不多全禿掉的,两眼看不見東西的老女人。在露台上坐著的人裏面,只有那老女人還有說話的能力,而且手還可以活動。 老女人還可以做一些小手功,送過她一些歪斜不對稱的摺紙花。 有時候,老女人會摸向她,尋著她的手,告訴她一些關於自己過去的事情。 曾經,老女人是一個小學中文教師。曾經,老女人有一個普通但幸福的家庭。曾經,老女人的丈夫在外面有了其他女人和其他子女。曾經,老女人有两個兒子。曾經,老女人的兒子都對老女人很好。曾經,老女人患上了眼疾,當時金融海潚,兒子們在股票巿場上被浪潮蓋過後再也翻不了身。曾經,老女人的小兒子跳樓自殺了。曾經,老女人的大兒子患上了肝癌死去了。 老女人凹陷下去的眼睛部分和滿佈皺紋的瘦臉始終保持著微笑,那仍然存在的幾絲幼小的頭髮,在陽光下透光,彷彿說述著的故事不是真的,而且很遙遠。 「今天也是好天氣。」老女人的手觸摸著陽光。 她對老女人所說的事,很多時候都只是一知半解。 擁有普通但幸福的家庭的感覺是怎樣的呢﹖ 結婚是怎樣的感覺呢﹖ 她連陽光曬在手上的感覺是如何也不知道。 每天,療養院也安排他們輪流看两小時電視。色彩繽紛,爆炸,强烈,舞動的各式廣告。電視劇中過著平常生活的人,說著不同的話題,自由活動著。那裏是跟療養院環境裏完全不同的世界,是一個所有東西都在動著,轉著,流動著的環境。熒光幕畫面上的一切影響在她的知識上,但她的知識沒有更進一步更深入更緊密聯繫的機會。她知道很多事情,也不了解很多事情,所知道的都只是浮面的光影。世界在電視機的框框裏展現,所有事情都好像薄煙的飄過。她看見一點世界的顏色,然後甚麼也沒有。 她不了解世界上大部分的事情。 世界上大部分的事情,不需要她了解。 世界上大部分的事情,那麼的遙遠,遠得永遠只能從電視機裏看見。 露台上,她正面對的牆壁本來是白色的,可是長久以來缺乏修繕,經過長年累月,已經到處留下了風雨侵蝕的痕跡。一道道大大小小黑色的水漬,墨綠色小點的青苔和漆油削下的裂痕。她看著那白色的牆壁由新鮮的白,一點一點的變化,每一次看見都可以發現上面有新的添加。現在白色的牆壁已沒有留下半點本來的樣貎。今天,她發現那已灰掉的斑塊部分重新長出黑色的霉,上面白色的石灰被霉嚼碎似的爆開。 從前,有一截水管需要由牆壁的這一邊接往牆壁的另一邊,水管安裝於穿往牆壁之間。後來水管被廢棄了,拆了下來,留下了牆壁上貫穿的洞口。無論是牆壁這邊的人,或是牆壁另一邊的人,也沒有在意過這洞口的存在似的,雙方也沒有提議或動手把洞口用甚麼方法填補或封死。於是洞口在水管清拆後一直存在著。只是,有一段很長的時期,牆的另一邊在洞口的位置放上了鐵板作為遮擋。鐵板的銹蝕也在這邊的牆壁留下了淡黃的痕跡。後來,聽說牆的另一邊的人要搬走了,那遮擋著洞口的鐵板也被搬走,洞口又貫通了两邊的風景。 她坐著的輪椅高度,讓她剛好直看向那牆壁貫穿的洞口。 還記得每年聖誕節的前後日子,牆的另一邊總是傳來人群集體合唱聖詩的聲音。唱聖詩的人有男有女,各人不同的聲音接合著,當中滲雜著各人對聖誕節來臨的奇異愉快的心情。她聽著聽著,覺得聖詩的聲音形成了温柔温暖的浪潮,隨著微風的推動,一下一下的輕輕拍打著她的心臟。那温柔温暖的浪潮帶她飄盪於温柔温暖的海洋,也讓她感覺著出生的起先,生命開始印象裏,曾經某人給予過的某種最甜蜜温暖的感覺。每當聽見聖詩的時候,她就比平日更好奇牆的另一邊會是一個怎樣的地方。她的想像裏,那一邊永遠設有一個合唱團使用的梯級形平台,人們唱聖詩的時候穿著天使的白袍排站在於上面,大家跟著音樂搖擺,就像在電視上所看見的合唱團一樣。 牆那邊的單位搬走了,遮擋著牆洞的鐵板也被移走,她終於可以透過牆壁的洞口,看見另一邊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牆的另一邊已經再沒有人唱聖詩了。那裏無論在甚麼日子,都是沉寂安靜的。那裏不存在她想像中的那個梯級形平台,她看見那邊的露台地板像蜘蛛網般的爆裂散開去,裂縫間隙長出了綠色的苔蘚植物和花草,而一些盆栽,因為缺乏照料,經歷過各種死亡的臨界點,半乾枯的枝葉擺出猙獰的姿態,又瘋生出狂舞似的綠色的生命,一種偶爾雨水帶來的奇跡,它們畸生,畸長。 在她想像中那個平台的位置沒有平台,現實中那裏站立著一個人。 那人和銅造的十字架一樣顏色。 十字架大約有三米高,站著的人大約有一點七米高。他的手和腳被釘在十字架的三個頂端,力氣彷彿早已洩盡了,身體無力的傾向下垂,形成死物被釘掛著的狀態。他的頭也是垂低著的,露出他的頭頂和他頭頂上戴著的帶刺的皇冠。低垂的頭,臉部全都掩藏於陰影裏,而帶刺的皇冠又經常在陽光之下放光,直射向人的眼睛。 人和十字架的銅氧化,青色的氧化物聚集於凹陷下去的位置又形成了向下流淌的樣子,青色的氧化物聚集於他的手掌,鎖骨,胸間,肌肉紋理之間,雙腳之間,像是青綠的血液曾經泊泊流過的痕跡。 他以這種姿態竪立於那邊,從甚麼時候開始,到甚麼時候結束,或到永遠。發出金光的皇冠,那些剌的尖端,堅硬銳利的直刺進人的神經,有時候知覺在不覺間顫抖。 幾隻黑色的小鳥在某個時段都飛到來,停在十字架之上,互相吱吱吱的停留一會兒,然後一同飛走。 她的目光追循著鳥的飛來,又追循著鳥的飛去,卻追循不能多久,鳥都飛離開了她的視線範圍外去了。 四處再次剩下了療養院式的有聲的沉寂。院友們因各式事項,用他們身體僅餘自由的能力表示反應,發出虛弱的近乎哀求的呻吟;護理員工作期間,踏著機械人般穩健生硬步伐的腳歩聲;第一輪的院友正在看電視,電視機在樓下大廳,傳來節目主持人的呢喃。所有聲音在各自的空間發出,互相迴響,訴說著相同的,生命邊緣上晃盪搖擺的語言。 在這有聲的沉寂裏,老女人開始訴說起從前教書時候的事。 她感覺著眼皮越來越沉重,老女人的說話嗡嗡,意義不明。剛起床不久,睏倦的感覺又再襲來。 昨夜隔離床女人的呻吟,護理員和醫護人員工作的聲音,腳步聲,開動儀器的聲音。她幾乎一整夜沒有睡。是其中一個原因。 上年冬季,她得了肺炎,斷續發燒了四天,曾經昏迷。好不容易的,醫護人員們把她救了回來,好不容易的,她康服過來。然後,她開始越來容易感覺到疲累。醒著的時候越來越短,睡眠的時候越來越長。有時候,甚致在無意的閉上眼睛的期間,思想停頓的剎那,她便無法抵抗的跌進了睡眠裏去。 這次肺炎康服後,也令她吞吃食物變得越來越困難。食物被放進口中,硬是被口腔失去了協調能力的肌肉迫出去,迫出去,只有少量的流質食物的纖維和水份,在肌肉壓擠運動的過程中偶然送到了喉嚨。流質食物的纖維和水份被蠕動到胃部,那只是身體飢餓的本能。然而,身體的另一種本能又向蠕動到胃部的食物作出排斥。飢餓的本能戰勝了要把食物排斥於身體外的本能,食物才被運送到胃部裏去。於是,她有時候會把辛苦吞到喉嚨的食物全嘔吐出來。每一次用餐,她身體的两種本能互相抗衡。 「她肝臟和腎臟的功能都有衰退的現象。」那天,醫生為她身體檢查的結果作出解說。 負責照料她的護理員在旁邊專心的聽著,眼睛的表面泛著奇異濕潤的點點光,但只有她發現著。 當天晚上,漆黑的房間裏,她床邊的小燈被開著,光線驅散她所在位置範圍的黑暗,把她從睡眠中拉出來。她看見護理員坐在她的床邊,臉上發出白色刺眼的光茫,而發出白色光茫的臉又顯得那樣的平滑,平滑得像日本傳統能劇中常出現的面具,純白平滑而僵硬,封閉著所有情緒。面具半垂著眼皮,背後的眼睛凝視著她。 她看著他面具背後瞳仁的半透明,冰冷的玻璃體。 她聽著黑夜中療養院另一種沉寂的聲音。 維生儀器在靜靜的運作。 人們在夢裏低吟。 過了很長的時間,他這樣的沉默的看著她。 然後,她看見那玻璃體在溶化,也泛著奇異濕潤的點點光。 她瘦得露出骨頭形態的手被他捉著,他温柔的掃撫著它,温柔的凝視著它,把它輕輕拉向他的臉。她的手沾著那玻璃體的溶解物。 「你知道嗎﹖」他低聲問。 「你是我的。」他低聲說。 「你是我的。」他再低聲說。 「你是我的。」他又再低聲說。 「你不可以死。」他最後說。 她看著他的眼睛。那裏有她不理解的瘋狂。 你知道嗎﹖ 你是我的。 她是屬於他的嗎﹖ 她不知道。 她是屬於誰的﹖ 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她的身體不屬於她的。 護理員幾乎一整夜坐在她的床邊,她也幾乎一整夜的在這樣的目光之下沒有合上眼睛,直到窗外滲著清晨的顏色,療養院的職員們開始交替值更。他離開前,吻了她的手,把她的手收回到被子下。 她看著清晨的光漸漸走入房間,又開始憐憫起護理員。 她的身體。 除卻她的眼睛,她無法控制身體的任何部分。身體和她的知覺分離。身體冷,身體熱,身體流血,她全都不知道。身體是附加於她意識上的物體,寄生於她意識上的異生物,依靠著她來維持生命和成長。身體和她各自獨立的存在著,之間的連繫,只有外觀上的幻覺。她常想像,她的身體和她的結合是一種錯配的結果。寄生在她意識上的身體是屬於他人的,而屬於她的身體也正寄生於他人的意識之上。 她的身體可能真的是屬於某人的,即使不是屬於某人的,也是屬於世界那邊的客觀物的其中之一。 而隨著時間的過去,她觀察著身體的變化,就好像觀察著近距離的任何客觀物變化一樣。 何時開始,身體某些地方長出了毛髮。下體的地方,毛髮長成了一個黑色叢林般的小島。 何時開始,那小島偶爾泛濫,流出紅色的河流,有時染紅了她的床單,有時染紅了她的輪椅。 何時開始,缺乏肌肉和脂肪的身體,胸肋骨頭憤凸的地方,平坦,甚致是微凹的胸部,乳頭脹大,慢慢的長出两個小小的如肉瘤般的乳房。 她好奇於這些變化。那寄生於她意識上的身體的變化,彷彿帶有著某種神祕的啟示。 而且,不單她發現了這種神祕的啟示,負責照料她的護理員大概也發現了這種啟示。 護理員對她的態度從那時候變得不同於以往,那種療養院式的機械化的與院友相處的方式,在她的身體改變的同時也開始改變。他僵硬的臉孔依然,目光卻徧離了機械的法則,那裏含有要跳越界限的巨大的焦慮和不安。 在沒有他人存在的情況,他大膽把他的手伸進她的衣服裏。 「雖然你不是她。如果你是她,那麼多好。」他撫摸著,說。 他向她經常談論「她」的事。「她」是他在每天下班乘巴士時遇著的女人。那女人擁有著染成棕啡色的長直髮,戴眼鏡,高瘦身材,有著甜美的笑容,手總是撥弄垂下的頭髮。 「她今天穿著黃色短衣,我認為好看是好看,不過太暴露了。或者是為了我才穿的,我喜歡是喜歡,不過還是太暴露。」他揭開她的衣服。 「我想知道她的名字。」他等待女人下車的時候,也尾隨下車,知道了那女人的住處。 「她會愛我嗎﹖她非愛我不可。因為我是那麼的愛她。我愛她,她也一定要愛我。要不,她是錯的。」他流著眼淚說。 一天,他們進入了浴室後,他關上浴室的門,並且鎖上。 浴室裏鋪滿了白色的瓷磚,空間四四方方的,每個角落有不同的用途。那邊是冷熱水花灑淋浴設備,然後是洗擦的地方,乾身和穿衣服的地方,一個為傷殘人士設計的馬桶。還有一張為方便護理員為傷殘人士清潔身體工作特別設計的椅子。 他先把她推到穿衣的地方,遠離花灑淋浴設備。接著他扭開花灑系統,扭到最盡的,讓水不停嘩嘩像下著大雨般的猛流出來。 室內迥盪著密密麻麻雨點落下的聲音,也彌漫著温水產生的薄薄的蒸氣。她看著遂漸聚集的水從淋浴的區域溢出,流到她的輪椅下方。他便來把她抱起,把她安放在那張特別設計的椅子上。椅子的外形類似牙醫診所讓病人躺著的靠椅,可以讓人仰躺著,身體傾向平躺,而椅子設有一條固定腰的寬帶,以防身體在清潔期間滑落。椅子的四隻腳下也設有輪子,方便護理員移動到不同的角落工作。 他的臉總是平靜的維持機械性的,為她解開鈕釦。 衣服被脫下,她的身體漸漸裸呈。 他的目光向她的身體凝視。一段靜止似的時間。夢遊人焦點迷失的眼睛,開始無意識似的自動化的行動,啟動起潛意識的欲望,釋放出內在的焦慮和不安。他伸手向她瘦弱的身體。撫摸,遊離,蹓蹥。他掬起她的乳房,輕搓著它,輕撫著它,手指按在乳頭之上,放開,又在乳頭上打圈。那像個游戲,也像個測試。他以一種學者的表情,研究她的身體,彷彿能夠在她的身體上得到珍貴的發現,然後在研究的過程,他愛上它,開始吻它。 他張開她的腿。然後又停止了一切的動作。他夢遊人焦點迷失的眼光放在她雙腿之間,那黑色小島的地方。貫徹他的探求,他的指尖潛入黑色小島。他望向那黑色小島,小心奕奕的,試途在黑色小島上有所發現。而後彷彿終於在小島上尋找著他的欲望。他要劈開小島。他把她的腿張得更開。接著,他急要看清楚他找到的寶藏,他要噬舐那寶藏,他把自己的頭臉貼在她的雙腿之間。他在夢遊的愰惚裏崩潰,潛意識的欲望從啟動的行為,實踐,浮面,在現實裏,尋求到了最大的滿足。 他低聲呼喊著一個陌生的名字。 那名字大概便是那女人的名字。 她看著身體被他如此對待,充滿呵護的,充滿瘋狂的,充滿不能自已的,充滿矛盾的。她看著她身體的皮膚泛紅,看著他的失去理性,發現它和他之間,那神祕的啟示讓他産生思想的迷亂。她覺得他很可憐,又覺得她的身體在某程度上,以他想要的形式拯救了他。 那小島偶爾泛濫,流出紅色的河流。 她知道小島的地方,有一個成長之後才被發現的洞穴。 護理員的眼光放在她雙腿之間。 她想著,也許他在她身體的洞穴裏也看見了她坐在牆壁前所看見牆洞那邊的東西,而且透過所看見的東西,他聽見了令他心臟搖動的聖詩。 然而,她的記憶中還有另一個霧般朦朧的影像。 影像裏,護理員在吞飲著她身體洞穴流出的紅色河流。抬起頭,他的臉是青銅色的,上面除卻有青綠的銅的氧化物,嘴臉滿是血肉,帶著欲望飽嘗滿足的呆滯。而她的身體,在她的意識上慢慢的消失。 她知道那是夢中發生的事情,但它幾乎恰到好處的和現實的情景重疊,有時候她也分不清哪是真的,哪是假的。 可能夢那邊的才是真的。 牆的另一邊,那個低垂著頭的銅像,臉藏在陰影裏。銅像的臉是護理員的臉。 「那邊的銅像的臉是護理員的臉。」她想告訴老女人。 聲音沒有從她半張開著的嘴巴發出。 老女人繼續嗡嗡訴說著…… 老女人一直以來訴說著自己的事情,大概也渴望得到外界的一點回應。而即使得不到回應,也希望聽見別人訴說一些關於自己的事情。她疲憊的想著。 如果能夠發出聲音,如果能夠說話,她會訴說關於那護理員的事情。她會訴說關於她們經常面對的那面牆的另一邊的事情,那裏的風景,那裏的十字架,那十字架上的人。還有那些經常飛來又飛走了的黑鳥。她會把所有所有訴說給老女人知道。她所能訴說的就只有那些。 她瞇著眼睛。 老女人的臉面向著太陽。失去了眼睛,所以才可以這樣。 老女人告訴過她,「古希臘的神話裏有一位太陽神。」 她嘗試看向老女人看的方向,强光更按低她的眼皮。 太陽神。 神。 神是甚麼﹖ 神是誰﹖ 今天的陽光有點怪,說不出哪裏怪,總之覺得跟平時的很不一樣。她覺得很累。 很累…… 嗡嗡……嗡嗡…… 很累…… 老女人的聲音變得細碎,跌入虛無…… 很累…… 神…護理員的臉…… 何時閉上了眼睛,光在外,射進眼皮,一片純粹黃黃紅紅發光的海洋包圍著她。她感覺到從未有過的疲憊,生命的動力正以某種方式流失到了一個陌生的盡頭,到發光的海洋的中心的黑暗裏。那裏正靜靜的旋動著黑色的旋渦,旋渦的深度直達未知的世界。她的意識毫不抗拒。 很累…… 很累…… 甚麼時候,那裏出現一隻黑色的鳥,那種平常看見的鳥,體型細小,羽毛黑亮的,叫聲有點兒像嬰兒的哭聲。鳥在旋渦之上靜靜的飛翔,然後飛向她,她和鳥相對望。她看進鳥的眼睛裏去,鳥看進了她的眼睛裏去。她明白了鳥,鳥明白了她,也互相明白了彼此相遇的目的。她疲憊的意識緩慢的走向鳥,鳥以比她行走的速度稍快的飛向她的意識。她疲憊的緩慢的伸出手去接觸著鳥黑色美麗的翅膀,剎那間,她和鳥緊緊擁抱在一起,大家跌進旋渦裏去。在旋渦裏,她和鳥相疊。 再從旋渦裏回來,歸向黃黃紅紅發光的海洋,她是鳥,鳥是她。她和鳥融合,鳥和她融合。她和鳥分離,鳥和她分離。鳥是鳥。她是她。鳥已是新的鳥,她已是新的她。 意識終於找著屬於它的身體。穿過黃黃紅紅發光的海洋,再次出世。 太陽正在天空之上,曬下蠟黃色的光,風流過羽毛之間,清爽又温暖,新的鳥在空中飛翔,眼看著下方。下方的建築物,牠有點熟悉。建築物两幢連在一起建成,之間只以一牆作為分隔,一邊是白色的沉寂的樓宇,露上坐滿了沉寂的人,或呆著眼睛,或溜轉著眼睛;一邊是露台已經被花草所佔據的樓宇,花和草在無人存在的環境下任意生長,充滿了生命的氣息,而生命氣息圍繞之間竪立著一個永遠受著痛苦的銅像。彷彿它所受的痛苦正正就是生命的能量來源。 白色的沉寂的樓宇,四樓的露台坐著的人當中,一個女孩歪著頭看向天空,正與牠對望。 真實裏,陽光下的她沒有閉上眼睛。她的眼睛已經冰冷,像覆蓋著一層霜粉的薄膜,隱約透露出內裏已然寂寂的空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