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註冊,結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讓你輕鬆玩轉社區。
您需要 登錄 才可以下載或查看,沒有帳號?註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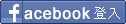
x
葉輝寫詩,老火熬湯,不時試味:一時說太淡,一時又說太濃。春秋更替、早寒晚涼。濃淡本無常,唯樂是味。鯨鯨詩集 : 「在日與夜的夾縫裏」,左右徘徊 , 終於在2009年與2010年間,揀選了時間另一道的「夾縫」出版了。
收在集內的幾十首作品,大部分我都讀過了。一首首讀,與成本詩集讀,原來是兩種不同的經驗:前者以詩論詩,猶如庭中賞木;後者以詩看人,則似曠野遇林。雖說作品離開了人,猶如母鷄生了蛋,味道如何,又與作者何幹?但我始終覺得,詩、人難以分隔。或者說,那是兩種趣味,不同的讀法。
比如說「廢郵存底」、「花鳥葡萄」、「一年只有這麼一天」這三首詩,或者更多,就令我讀倒作者感情內歛的一面。「廢郵存底」與「一年只有這麼一天」固佳,但不及「花鳥葡萄」來得隱約與自然。這首作品描寫有意的疏離與無意的重逢:表面瀟酒,難掩浮城的寂寞。我與她,也許就是百貨公司這迷宮的上層與下層,不見於電梯與出口,終見於半生的床。花鳥與葡萄,不就是人生夢與現實的隱喻。作者活在其中,又嘗試跳出,回顧這樣一種微妙的關係。與這一些詩對應的還有另一組的文化詩 :「蓮之食譜」。所謂語帶相關的文字遊戲:以此喻彼、虛實交纏、睹物思人等等,作者實在優而為之,不讓學院專美之餘,恐怕更有生活的質感。譬如:
「看不見你鳥衣底下深情的肌膚/包孕着泥漿裏茁長的細緻筋肉」(佳偶天成);
「你以靜默容忍着勸飲的醉意/魚腹尺素,飽吃才知長相憶」(開枝散葉);
「窩心的羹茶,淡淡的齒頰餘香/總是白了頭才懷念偕老諾言」(年生貴子)。
這幾首詩真是化傳统為現代,寓食物以深情,將來或有食店將貼招徠,風雅其事,亦未可知。
讀詩不是索隱,有時又不得不索隱。「紮作店的老人」、「彌敦道」、「碼頭」、「小鎮墓園」與「兒子的心事」,可視為作者成長的故事。「紮作店的老人」是葉輝早期最原創的作品之一。裏面不單止寫人,而且印記往事,小店主人30年就像紙紥的一生:平淡也罷、寂寞也罷,他與他的那個時代,就是這樣過去了。記敘粗疏中有工筆、概括中有細緻、冷眼中有同情。所謂共生共長,還見諸終以下的具體細節 : 「父親給我買了草綠的帆布書包 / 你檢拾拜祭文曲星的衣紙 / 粗厚的手撫着我的頭 / 五歲還是六歲?進學校很快就要長大了……」從「紮作店的老人」到「彌敦道」,成長好像突然間換了場景,小學生變成了學師仔,又居然懂得 : 「用隔夜收藏的布碎 / 剪裁偷師學懂的時裝 / 給七姨的洋娃娃 / 他們在皇上皇吃一客常餐 / 在新華戲院排長龍……戲票呢,他說,放在銀包 / 連同他和七姨的合照 / 師傅的掛號,都給文雀扒走……」。這是詩化了的童話,內容也許是借喻,也許是嫁接,但又有甚麼關係?反正那個年代的荳芽夢,像跌碎的水晶球,晶瑩四濺,只要願意撿拾,也就人人有份。
長大的印記,其實還包括某一種生活的挫折與張望:所以讀到「碼頭」中這樣的細節,我特別感同身受:「二房東沒有催租 / 可是老聽到他在客廳踱步 / 下班只好約妻子到碼頭 / 看海,看船來船去……」;所以「兒子的心事」中,一個傳统父親這樣隱晦的表達,就更牽引動人:「他有一天故意喝醉 / 對兒子說 / 幫老竇一個忙……兒子給他敷熱毛巾 / 在朦朧的燙熱背後 / 點了點頭……兒子終於代老竇實踐了 / 耽誤了廿多年的諾言……阿爺插了遍體的喉管 / 躺在那裏三年有半 / 再沒有氣力睜開 / 彷彿融雪的眼簾 / 見識家族裏第一個 / 大學畢業生……」葉輝大部分的作品,都殘留經營的痕迹,唯獨是這一首交織三代,輾轉呼應,一氣呵成,誠為詩集中最優秀的作品之一。
寫詩要有生活的實景:實景輕,詩也輕;實景厚,詩也厚,此所以有「兒子的心事」之積厚而薄出。但只是景,有時也不夠,還要閱讀與思考。移民這一段時間,寫得最好的作品應是「小鎮墓園」。這首作品記叙一次迷途,而發見另一個隱藏的墓園世界。墓園與人間,存在與不存的交織,既互相依附,又不斷地各自伸展,令詩變得豐厚。試讀這一節 :「鑿石工說從沒聽過那條街的名字 / 說打個電話回去叫家人來接吧 / 他遞來一杯茶 / 還他一根煙 / 看他在碑上鑿刻惠特曼的輓歌」。這一節用的是白描,與他相對,好像就在與另一個世界相對。鑿石工不熟悉現實世界,正如迷者對墓園的陌生。整首作品的思考性很强,但流露十分自然。不寫迷途的彷徨與焦慮,而另闢蹊徑,這樣偶得之作,以後不復見。
索隱不過是解讀的其中一種手段,讀其詩如見其人。此外,搭了戲棚,讓詩有了一個表演的地方,看的人也踏實。當然,亦有人喜歡看沒有戲棚的戲。比如洛楓寫了「詩與電影的對倒」鯨鯨的「花樣年華」組詩;鄭慧如寫了「評介「我們生活在迷宮那樣的大世界」。我,自然也讀出了這類詩的趣味,但焦點不在文化、知性的反思,而在詩藝機智的展現:「你有你錦衣夜行的哲學 /我有我裸體抗命的公民 /就是不明白前世的繁殖 /何以觸犯今生的公安法」(見「龜怨」第一節)「隔着塵封的玻璃 /我唸我無音之經 /你流你透明之血」(見「珠蚌」第一節)其實,類似的機智寫法,也見諸於其他的詩作,如:「我們的頭顱 / 這一天終於淪陷了 / 每張臉孔的下游 / 都覆盖着一方 / 小小的白旗」(見「我們的頭顱這一天終於淪陷了」第一節)。前述「蓮之食譜」更不時閃現,篇幅所限,這裏就不引了。
談到詩藝,葉輝知之甚深。而知,不止傳统,還有西方。讀他的詩評,總見到對西學的轉化。因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甚麼作者總不會停留在某一種的形式:從早期四四三三的西方十四行,到後來的二行一節,七節一首的變化十四行體;那怕在「花樣年華」的組詩中,也見到有四行一段與三行一段的兩種刻意安排;而「童年的房子」、「默哀三分鐘」與「我用肥皂水替她除下最愛的指環¾¾給母親」,又嘗試變用散文體。這明顯是「讀而通則學」,通過實踐去與內容互動。現代詩究竟有沒有格律?葉輝一糸列的實驗性作品說明了¾¾「有」。需不需要?「需要」。但同時又應該清楚、明白,那不是古典「定於一」的格律。如果解除了「蓮之食譜」、「花樣年華」以及「我們生活在迷宮那樣的大世界」裏面的格律,詩的藝術性、欣賞性必然大減。詩,有時是要帶着脚鐐跳舞方好看的。葉輝從九十年代初開始打造個人的形式,至今二十有年矣,所謂何事?不就是一如其他人,希望拉開香港現代詩的闊銀幕?說是沒有用的 , 所以他頗有耐性地寫了這一本不算厚的詩集 .
寫寫停停、讀讀翻翻,也就過了兩天。往事如塵,卻又隱約可見;你說到我們這個年紀,毋須由別人來肯定了。但書成上架,那一種俗人的喜悅,我們還是有的。延續高興,故不妨書寫推推 , 與有榮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