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註冊,結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讓你輕鬆玩轉社區。
您需要 登錄 才可以下載或查看,沒有帳號?註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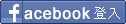
x
不論生活在什麼地方,你的童年記憶,你的生活的根,都是你的創作和精神家園。
劉以鬯、西西、也斯的書還在賣,但他們書裏的故事與經驗,已經跟香港年輕人比較遙遠了。
現在是香港文學、文化非常重要的轉折期,怎樣把以往幾十年的那種經驗跟現在的年代磨合得比較好,還需要年輕作家的努力。
葉輝,本名葉德輝,1952年生於香港,上世紀70年代投身新聞出版事業,業餘參與文學出版及編輯工作。1976年與詩友創辦《羅盤》詩刊,1984年接任《大拇指》(初為雙周刊、後改為月刊)文藝版編輯,並參與《秋螢詩刊》、《詩潮》、《文學世紀》及《小說風》的編輯工作。《水在瓶》、《浮城後記》、《書寫浮城》、《煙迷你的眼》、《新詩地圖私繪本》曾分獲香港第五屆、第六屆、第七屆、第九屆文學雙獎。
葉輝,年齡當然比不過年過九旬的劉以鬯先生,也比生於1938年的西西年輕很多,卻依然被評論家尊為香港的「文學前輩」。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葉輝就以詩成名。從上世紀60年代末開始文學創作,盡管他後來長期從事繁忙的新聞業,但也不改文學情懷。尤其是近年來新著不斷出版,他在香港推出的《最薄的黑最厚的白》,在臺灣推出的《昧旦書》都格外引人關注。日前,他在香港接受了晶報記者的專訪,回顧了自己的創作歷程,也坦述了他對香港文學的看法。
晶報記者 莊向陽 實習生 吳燕雲/文 雨希/圖
我向左右兩派學習
晶報:有文學評論家尊稱你為「文學前輩」,那麼,你是怎樣開始創作的?
葉輝(下簡稱「葉」):那是1968年,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我去了一家假發廠做暑期工,負責把那些頭發梳順。廠里有一些女工,她們看一張叫《娛樂新聞報》的報紙,版面上有塊「讀者園地」,談你喜歡哪個明星,我喜歡哪些明星,上面也刊登一些類似詩和流行歌曲的東西,那些女工說它們寫得很好,我跟她們說,我也會寫。青年中心的閱讀室有幾架書,不用排隊,我在那里看了何其芳、馮至、卞之琳等人的詩集,有些印象。所以我一看娛樂報上那些說是詩但是差不多是歌詞的東西,我說我肯定會寫。
那個女工不信,她以為在報上寫東西是很了不起的,我們就打賭,我說我今晚回家去寫,寫了後你替我寄出去,五天以後我的詩原原本本、一字不改就登出來了。那時我才16歲。
晶報:這對你是很大的鼓勵。
葉:她們以為,你怎麼這麼天才,能寫這個東西,中間有幾句我們還不太懂,其實也不太難,只不過把一些徐誌摩和何其芳的句子重組了一下,可能中間有一些詩的象征吧,女工看不懂。我在工廠里變成一個小名人,五六十人的工廠,從女工、師傅到老板對我都很好,都把我當作一個天才。回到學校後我開始投稿,但投稿了才知道自己不行,很多較正規的報紙,你投稿了它不一定登;而且,寫徐誌摩和何其芳重組的句子,模仿階段很快差不多了,要寫自己的話,自己的東西時,找不到自己的話。起初以為自己是天才,後來經過七八個月,不斷給人家退稿。
後來我碰到一個《青春周報》的編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有左派、右派兩條文學路線,左派要求抒情也要抒健康一點的情,抒情還要有一點現實的底子,不能憑空地、很虛無地去抒情;另外就是受臺灣影響,臺灣的現代主義、西方的現代主義對香港文學也有很大的影響。兩條路子我都走過,《青春周報》的編輯是從左派系統來的人,他說,你的基本文字是不錯的,但是寫得太頹廢,里面也沒什麼東西,空空洞洞的,他就從頭教我,怎樣貼住事情來寫,貼住人來寫,貼住你自己的生活來寫,我覺得他講的雖然有一些教條,但也並不是沒有道理,如果沒有現實底蘊、生活底子,說什麼都是虛的。所以我兩邊都學習,我把左派的《青春周報》那種比較現實、比較生活、比較健康的東西,變成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也受西方現代主義影響,他們有一些想法就是不一般,比如卡夫卡的小說對我的影響也很大。我起初分不清,明明不是現實,為什麼還有一些評論說這樣的寓言,這樣的「變形記」會變成現實,那時候我年輕不明白,後來到20歲左右,我摸索了兩三年,才想通了,兩者之間原來是有道理的。如果光說現實主義,寫來寫去太老套;如果沒有現實主義的訓練,光寫很虛妄、很荒誕的東西,沒有底子,里面都是空的。怎樣去調和,變成我自己的東西,就是我長期去學習寫作的一個出發點,我在16歲到20歲的時候,就是思考這個問題。
童年記憶就是精神家園
晶報:回顧過去幾十年的創作經歷,你認為可以分成幾個階段?
葉:先是1970年到1982年,這是我認識自己的階段。起初寫作的時候光是寫,沒想我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很多人的籍貫寫的是廣東、安徽等,但寫出來的東西非常陌生,不像香港這個地方對你來說這麼真實。這個階段大概就是我去思考我是什麼人,中間慢慢認識到本土是什麼東西,本土的意思就是,不論你生活在什麼地方,你的童年記憶,你的生活的根,都是你的創作和精神家園,這個階段大概就是慢慢地把寫作跟本土搞清。
第二個階段是 1982年到1990年,我辦過兩個刊物,一個是青年文學刊物《噴泉》,還有詩刊《羅盤》。1982年我還參與一個叫《大拇指》的刊物,我起初是讀者、作者,1982年我接手去編這個刊物,成為編者之一,這個階段我主要是調和,因為我編的時候希望不分派別,不同的想法的人,不同文藝思想的人,我都邀請他們一塊寫稿,包括香港的,臺灣的,最多的還是內地的,顧城、歐陽江河、翟永明就是這個時候認識的。我們也辦了一個詩獎,不管你是哪里人,中國內地的、臺灣的、香港的、海外的,都可以參與,那些評判也來自不同地方,顧城也拿過這個詩獎。這樣的一個過程跳出了本土,應該是不同地方的漢語寫作都匯聚在一塊,大家互相交流。很多朋友到報社工作,他們叫我去寫專欄,寫專欄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香港很多主要的報紙我都寫過。這個階段回想起來是一個很好的成長經驗。
1990 年我移民到美國波士頓。移民有個好處,在那邊找不到好工作,有時候回來兩個月,有時候也過去幾個月,主要還是閑下來讀書。波士頓有很多有名的大學,包括哈佛、麻省理工等,大學里面圖書館非常好,有很多美國東部文學的傳統,很多美國有名的人都是東邊的人,包括弗洛斯特、狄金森。我後來知道,為什麼他們寫的詩會變成那樣,因為冬天茫茫大雪,全世界好像靜下來,只有你腦袋里的東西還在動。在這樣的環境里讀書,讓自己的心靜下來,從1991年到現在算是第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我是慢慢認識本土,第二個階段認識本土以外的漢語寫作,第三個階段在漢語寫作之外認識這個世界,很多人是怎樣寫作的。這樣三個階段,對我來說,每一個階段都有影響,綜合來說,就是從井口慢慢看出去,本來是井口上一小片天空,走出井口以後,登上山後,看得很遠,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看法。
晶報:你不僅是一位作家,還從事過很長時間的新聞工作。
葉:我大概是1974年起在報社工作,先在《明報》當突發新聞記者,後來去搞《體育周報》。1978年我進了《東方日報》,從記者到編輯,然後到編輯主任,1990年我就離開了。移民到美國後,東方的老板讓我回來,搞《東方新地》、《東周刊》等八卦周刊,1996年老板讓我去當《東方日報》的總編輯,從 1996年到2004年都是做報館管理的工作。我每天都工作十五六個小時,很累很累,2004年我就不幹了。2006年當《成報》社長,搞改革,報社很窮,但有很大的自由度,做得很有滿足感,還找到西西、梁文道等作家寫專欄,可是報社沒錢,連員工的薪水、稿費也發不了,半年後便幹不下去了。我去教一點課,每周寫一篇專欄,我要求自己,每個星期頂多工作四天,只寫四篇稿,每天工作四五個小時,其它時間去讀書,看電影,這樣的生活到現在為止,四年多了,我覺得還是很好的,對這個狀態比較滿意。每寫一個專欄,基本上是我寫一本書的過程。
你喜歡就一點都不辛苦了
晶報:你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進入新聞業,那麼忙碌,為什麼還能寫出很多作品,甚至詩?你是怎麼做到的?
葉:七八十年代我能寫東西,主要還是家人對我很寬容。在報社沒有做總編輯、社長以前,我每天都是淩晨兩點鐘下班,回到家,老婆就做了些東西給我吃,然後她就去睡,每天從兩點半到三點開始,到早上六點半左右,很靜,什麼都沒有,沒有電話,沒有網絡,只有書、音樂、寫作,這樣的狀態維持了七八年,我每天都堅持寫作,《昧旦書》就是那個時期開始寫的,「昧旦」,其實是蒙昧而未旦,是沒有天亮的意思。每天有三四個小時非常集中地去想,去寫東西,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我天亮才睡,睡到中午後才起床去上班。
晶報:你的意志力很好。
葉:也不僅僅是意志的問題,你喜歡就可以了。如果你喜歡,你真的喜歡,你去畫畫、音樂,你不一定能夠成為畫家、音樂家,寫作,你不一定能成為一個好的作家,你喜歡就可以了。你喜歡就一點都不辛苦了,這是你的愛好嘛。如果你覺得看書很累,看書看得那麼辛苦,寫一篇文章才幾百塊,那你就覺得非常辛苦;看書是你的愛好,反正你寫不寫這個東西,你還要讀書的,讀書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一點都不苦。
晶報:剛才談到《昧旦書》,為什麼早就開始寫了,卻到現在才出版,這次是在臺灣重版嗎?
葉:不是重版,對我來說這是非常有紀念意義的一本書,文學性較強的一本,也是我在臺灣出版的第一本書。臺灣秀威出版社要重組,約我給他們三本書,這是其中一本。書中文章的寫作時間大多是上世紀80年代到2000年以前,此外加了大概十篇新作,算是我的自選本吧。
不是每一個專欄都是文學
晶報:香港作家很了不起,每天寫一點在報上發表,然後連起來是一本很棒的書,這是否要求作者對未來要寫的東西,要有很好的構想?
葉:對我來說,寫專欄是很好的訓練,你答應了人家,就如結婚時的誓言,「不管貧窮還是富有,不管健康還是疾病,我都不離不棄」,寫專欄就是這樣的一個承諾,除了過年的幾天你可以休息,否則不論你快樂不快樂,有病沒病,你每天都要交稿。如果你沒有很好的計劃,沒有很好的心態,你也可以亂寫,但是你還是要給自己一個承諾,起碼我要怎麼樣,我定一個最低的標準。人們說專欄文學,但不是每一個專欄都是文學,你一定要有堅持,才能把專欄的文章整理成一本書,才是一本有價值的書。
晶報:你剛剛提到「專欄文學」,香港寫專欄的有很多,但是能把專欄結集成一本書,一本讓讀者認可的書,就比較少了。
葉:比較少,但也不是沒有。西西主要的小說,基本上是先以專欄的形式連載,《我城》就是這樣寫成的。陶傑也是寫專欄的,他早期寫他在英國讀書見聞的散文也寫得非常好。董橋的書,基本上也是在報紙上一篇一篇寫出來的。林行止,也是一篇一篇專欄寫出來的。以上幾位寫得好的東西,都是他們自己認真寫出來的,跟載體無關,不是說在文學雜誌上刊發的才是寫得好的,或者說給報紙寫的不好,不是載體的問題,而是作者心態的問題。
晶報:你最初是從寫詩走上文學之路的,是什麼時候轉到專欄或者說散文寫作上來的?
葉:大概是我當記者以後,在報紙上寫出來的那種新聞,對你來說一點也不滿足,你見了什麼,你就要報道什麼,是為了讓讀者知道,但是在採訪的過程里你有很多感受,你就把那些感想用記事本記下來,這種筆記,就是一個很好的專欄訓練。
新一代在尋找自己的文學道路
晶報:很早以前就讀過你的詩,記得周良沛主編的《香港新詩》一書里就收有你的《微辭》、《格子和煙屁股》。讀那本書,我還發現,原來香港當年有那麼多人在寫詩。
葉:現在也有很多人在寫詩,從2003年到去年,我跟關夢南編了《秋螢詩刊》,是月刊,我們很準時,每月一日出版,辦了7年,84期,現在香港寫詩的青年人基本上都是這個詩刊訓練出來的。我覺得寫詩是一種很好的語言訓練,但我跟學生說,不要像一些詩人那樣,有一些詩人詩寫得很好,因為詩是一種非常濃縮的語言,它是鳳爪,不像鴨爪一樣中間有一個蹼連在一起,五個句子就是五個手指,可以變成一首詩,但寫散文需要文字連起來變成一篇文章,長期寫詩可能是壞事,我很多朋友寫詩,但他們連一篇比較通順的散文都寫不出來,最主要還是那種語言的長期訓練下,習慣了那種語感、語調,要寫一篇準確的記敘文,中間有很多東西都不懂得表達。
晶報:您上世紀70年代開始走進香港文壇,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四個十年,您覺得香港文學的變化趨勢是怎樣的,變化大嗎?
葉:當然變化很大。上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外來的老作家影響很大,他們都是1949年前後從上海,從不同地方來到香港,他們懷念的都是過去,寫過去,寫北平,寫他們的故鄉。這樣的東西對我來說沒什麼感覺,並不是我不尊重這些老作家的寫法,而是我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和體驗。50年代到70年代基本上是意識形態鬥爭很激烈的年代,是冷戰的年代,80年代到2000年,是香港前途問題,開始有人對「一國兩制「比較抗拒,慢慢地認同,懷疑慢慢減少……從冷戰的年代,意識形態的懷疑,到我是本土的,我是香港人,香港的本土是什麼,這樣的一個過程就形成了香港不同時期的文學。文學,不可能跟時代跟社會完全無關,沒有這回事。
現在,從劉以鬯,到西西,到也斯,他們的書還在賣,但他們書里的故事,他們的經驗,好像跟香港這代年輕人比較遙遠,七零後或者八零後的那幫人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一個生活,他們也要建立自己的聲音,尋找自己的文學道路,所以我說,每一代有每一代的文學,香港現在大概正處在這樣的轉折期,新的文學還未具有規模,還在建立,那套舊的文學經驗也有一些變通、調整,想辦法跟現在這個時代相適應。所以,我以為現在是香港文學、文化非常重要的轉折期,怎麼樣把以往幾十年的那種經驗跟現在的年代磨合得比較好,我看還需要年輕作家的努力,等他們的經驗慢慢沈澱下來,才可以看出端倪。
晶報:香港的年輕作家中,你比較看好哪幾位?
葉:如果是小說家的話,我喜歡的有謝曉虹,她有本小說叫《好黑》;還有韓麗珠,她最近這幾年寫得非常努力,書在香港出得不怎麼好,她到臺灣找到一條出路;我覺得鄧小樺也寫得不錯,她的那種路數跟前兩個人不一樣,她主要還是社會參與比較多;再年輕的,還有李維怡,她寫小說,也參加社會運動。還有雨希,她很善於用場景來說故事。這幾位都是30歲左右,前幾位是1977、1978年左右出生的,雨希是80年代出生的,都可以算是廣義的「80後」。
附錄:香港文學KAIROS的回應
徐偉志(香港大學文學碩士)
葉輝的文字是耐看的。他是香港文壇的北野武。但凡接觸過葉輝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博學、雜學。他寫詩,寫散文,《Kairo:身體、房子及其它》是他的文學評論集。
Kairo 源出古希臘文字,大概的意思是千載難逢的機緣。葉輝把它理解成「黃金入球」,看來他是個球迷了。Kairo與身體、房子那麼具體的名詞撞擊出八部文集的序言,包括洛楓的詩集《飛天棺材》,崑南的詩集《詩大調》,王良和的小說集《魚咒》,也斯的《剪紙》,謝曉虹的《好黑》等。千百年來,我們一直在重複著過去的故事,這就是我們的Kairos。葉輝寫道:「我生故我在,我死故我也在,這套存活狀態,我決定了,我必須稱之為Kairos」。身體與房子,前者是我們靈魂的居所,後者是我們身體靈魂的共同居所。
閱讀葉輝的文學評論,是一次學術殿堂的回歸,在評論王良和的身體系列小說時,他運用後現代文學理論來進行解讀,其中提到了柏斯與福柯關於身體的理論。葉輝這樣寫道,「身體堪可被理解為一個交纏著時間與欲望的隱喻」,當讀者聯想本書的題目後,對於身體這個容納著時間與欲望的場所當有進一步的想像空間。葉輝以故事原型及希里斯·米勒及本雅明的敘事理論,來解讀謝曉虹的小說作品。文章的最後一句足以使我們深思:「一千零一夜講述下去,大概就是說故事的人窮其一生沒完沒了的未竟之業。」
葉輝以「計算機複制時代的鏡象和餘留物」為也斯的《剪紙》為序。葉輝這樣寫道:「這是我第五次細讀《剪紙》了。」1977年是第一次閱讀《剪紙》,1982年第二次閱讀,1987年第三次閱讀,1988年第四次閱讀,2002年是第五次閱讀,今年是2011年,是否有第六次的第六種讀法?如果接觸過也斯《剪紙》的讀者都明白「剪紙」的「剪」是動詞。葉輝是這樣寫的:「小說中的『剪紙』和貼版工作有極濃厚的『實況』意味。從前從事傳媒工作是有形的剪刀,現在計算機時代無形的剪刀,都進行著同樣的Cut & Paste,剪下無中生有的謠傳,貼於無辜而無助的對象……」葉輝用鏡象解讀,《剪紙》就是高懸的鏡子,照見人間色相,難怪葉輝說每次讀它都有不同層次「社會實況」的體會。
葉輝的《Kairos:身體、房子及其它》雖然只論及八位作者,不過,仍然可以看作是香港文學的一個橫切面,此書的面世,似乎也正是香港文學Kairos的呈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