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註冊,結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讓你輕鬆玩轉社區。
您需要 登錄 才可以下載或查看,沒有帳號?註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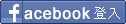
x
異域殘月之夢
施先生常做噩夢。那種夢,做的時候不覺可怕,醒過來回憶,施先生總是不期然的冒冷汗。他常做那種夢,常回想那種夢,從來沒有習慣過來。他近來夢見了這些:
夢一。
驀然從床上起來,聽見鏗鏘金屬掉落地上的聲音,嗡的作響,還未停,施先生但見一元硬幣自轉滑旋,良久不停下來。是公還是字?他突然想起這問題。還未停下來,他走近它,旋轉的影像如蜂類高速飛拍透明翅膀,欲踏停那一元硬幣,一踏之下,挪開腳,無影蹤。
卧室看來有點奇怪。書架旁邊多出一隻窗,加上原來存在的窗,兩隻窗一明一暗。
明亮的窗是明亮的風景,兩幢樓宇建築物靠近只相隔一條狹缝望見另一邊的窗景,於是是別家人戶內的環境。可不像是家庭的裝潢。他認得那兩盆自他入行便一直擺放在公司門市部店舖門前的人造棕櫚樹,人般高,葉子以打蠟劑噴擦,多年來新鮮翠綠,一塵不染。多少客人誤以為是真樹,看著看著便自然伸手去摸它們的葉子,還是以為真的,連樹幹也摸,也研究盆中的泥土是否有根。施先生習慣站在其中一棵棕櫚樹之下迎接客人,每天先在那裏的長鏡子前再整理一身的西裝,合身的西裝外套,西裝褲熨得筆直的,身材徧瘦,保持微駝背,讓他永遠看起來謙卑温文,永遠的微笑,使他親切容易靠近。
「施先生。」一個下屬在窗戶裏叫他,靠在窗前,遮住一棵棕櫚樹。
忘記有如此一位下屬的存在,未想及那人叫甚麼名字,施先生不自覺地笑起來,向他揮手。
接著,那窗戶裏陸續出現其他下屬,都一一叫過施先生。
暗黑的窗仍在,是無端多出的窗。他得走過去看那暗黑裏頭是甚麼。臉貼上窗的玻璃,唯見一片暗黑,想著打開窗戶,窗戶在下一刻自動打開,他伸手出去,竟抓著室外垂直下來的暗黑布簾。揉抓布簾,揉抓著,揉抓著,長長的,好不容易掀起了一幅,又是另一幅暗黑的布簾,於是他又揉抓布簾,比之前快手,但暗黑布簾一幅又一幅出現。
一元硬幣掉落地上的聲音。
放下那重重布簾,施先生停住了,往室內四處觀望。揉抓進室內的暗黑布簾躺於地上如穿著黑色芭蕾舞衣的舞者屈膝於地上等待舞曲奏起,翩翩起舞,它翩翩起舞,以優雅的姿勢一躍而跳,跳回出窗外。暗黑窗戶三維的視察效果減弱,越益模糊,變成二維世界的圖像,兒童拙劣簡陋的圖畫。某種强大的力量如暴風,把它搊成一個巨大的黑紙團,轉動,轉動,鑽進牆壁中。無由來的不安感,施先生嘗試忽略,卻不成功。還未弄清楚到底發生甚麼一回事,「啪」的巨響,光明的那窗戶一片空白,影像如化於水裏,刹那不見蹤影,也如剛才暗黑窗戶的樣子,鑽進牆壁中。
若有人闖進房間,房間只得一個藏身的地方,牆角那個高頂天花板的衣櫃,澄黃柔和的木色。施先生靜靜靠近那衣櫃,想像著闖入者隨時從衣櫃衝出來,或者是闖入者於衣櫃內任何身體微弱的移動產生一點聲音,施先生便可以知道衣櫃裏確實有人。他傾耳到衣櫃門前,沒有絲毫動靜。那人可能有刀。施先生立刻退後一步。這時衣櫃門自動緩緩打開,施先生瞪大眼睛,內裏甚麼也沒有,連本來擺放著的衣物都不見了。施先生認定是小偷所為。
思想迷矇間,耳邊嗡嗡作響,囈語般的話語呢喃,又像是某人怨毒寂寞的詛咒低吟,卻十分熟識,與不安的感覺緊密連結互相牽動,施先生有點恐懼,又好奇於聲音的來源。循著聲音的强弱大小,他認定是由衣櫃裏發出。耳朵靠進衣櫃裏,他整個人躲進衣櫃裏去。白天汽車行駛於馬路上的聲音,電話鈴聲,客人的粗言穢語,他低聲道歉個沒完沒了,女下屬被罵哭的嗚咽,他的安慰,其他下屬七嘴八舌罵著客人,母親夜裏的咳嗽,徹夜的咳嗽,帶著痰涎的呼喊他的名字,還有很多很多分辨不出的聲音,一串連抽扭著於他耳邊旋轉交替,時而這聲音,時而那聲音,重重疊疊密密麻麻,嗡聲嗡氣。他受不了,從衣櫃掙扎跳出來。
房間給他的感覺既熟識又陌生,明明感覺著身處於自己的房間,房間裏的一切都似乎與印象中的不同,可又說不出不同在於哪裏。房間看起來越來越小,四面的牆壁往他移動進迫,不一會兒,已移至他的鼻尖前。本能反應使力推向牆壁,牆壁依然向他壓迫,沒有絲毫減慢下來的跡象。他發現手插進了牆壁裏,摸不著建築物料水泥或磚頭,連粗糙的沙粒也沒有。牆壁表面亦不是破裂開,而是像一層薄膜被穿過凹陷下去。把雙手抽出來,薄膜又成磚塊砌成的模樣有了堅硬的質感,如石頭般裂開一條縫隙,縫隙立刻漫延,漫延向四邊,牆壁一塊一塊嗦嗦剝落,崩潰,嘩的一聲噴湧出鮮血。施先生閉上眼睛迎上這血泉,感覺不到,於是又睜開眼睛。血泉仍正在湧進來。
照理是應該滿臉滿身鮮血的。他身上一直穿著上班慣常所穿的衣服,白的還是白,黑的還是黑,不沾一點紅,也沒有被沾濕的感覺。鮮血灌注他的房間浸至及膝,就像是大屠房放血流入渠口渠道的終點地。血從哪裏來的?半躺於自己的床上,望著血泉濃紅濃黑的,心裏竟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平靜,如身處的地方其實是晴朗日子的海邊,思想在微風中停止。之前的不安感不知怎樣的消失了,他也記不得曾經有過不安的感覺。
夢二。
天空橙紅,是黃昏最濃的顏色,紅得刺眼,紅得耀眼,如對倒的血海。
荒地,遠處俯伏著幾座荒山,腳下盡是乾旱龜裂的土地。龜裂縫間一些早前長出的草也已經枯死,留下蠟白色,中空的軀榦。天上沒有雲,也不見太陽和月亮,他感覺著太虛無物的平靜。這裏像是萬物的終點,宇宙的盡頭,時間和空間被放遂,到處飄浮著太空殞石,漫無目的。
地平線鼓動,震撼太虛境,一切景物出現重影,那是萬物的悸動。一直不平服,一直不平服,到平服時,地面開始下陷,山開始搖動。龜裂的土地一塊塊墜落地底,萬丈深淵一吋吋呈現,一吋吋擴展。跌墜無聲進行,漸形成一個橫越荒地的巨大無底洞,看下去只有黑暗。地靜止,山靜止了,鼓聲又再震震從遠方而來。深淵巨洞邊緣紛抓出雙手,爬出個人,一人爬出來,另外一雙手抓出來。人數不斷增加,不同膚色的人種,面無表情的,都眼眶凹陷沒有眼睛。他們一走上地面便走往同一方向,腳步躝跚,或跌或撞,沿途掉三漏四,滿地東西。
施先生蹲下身子,欲為他們執拾,近看之下,悚然心驚,像豬的皮肉,一片片,一堆堆,全由人的身上掉出來,那便是人的皮肉了。行走中的人群,皮肉每掉落,身體上便出現紫黑傷口。有的人已經差不多渾身變成了紫黑色,剩下半個頭顱,三份之二個身體,單憑一身可見的白骨支撐,蹭蹬於路上。
一人竟還留著一隻眼睛,不過眼皮脫落了,全紫黑色的頭顱,一顆圓眼球特別的在上面,像是蛋糕上的士多啤梨般被安放著,只是它是白色的,而且是活的,黑瞳仁骨溜移動。他搖搖晃晃跳舞似的向施先生走來。施先生大駭,想轉身逃走,可無論如何還是動不了身,頭也定住的,瞪著眼睛看著那人慢慢向自己靠近。除卻那顫巍巍的眼球,在到處尋覓焦點的瞳仁,施先生還看出他紫黑面上沒有了的嘴唇向上彎。
「害怕甚麼?你不也一樣嗎?」瞳仁突然安定下來。
施先生從那瞳仁的映照看見自己缺了半邊臉,伸出手也是缺了幾根,皮肉鬆垮掛著,全己紫黑。感覺不到一點痛楚,因為不痛楚,這些可怕的影像漸似尋常,施先生模糊的思考邏輯想著這些事是經常看見的,沒有甚麼不妥。
「走吧。」那人說。
他們成為同伴,成為其他人的同伴。
走往哪裏,哪處是目的地,似乎都不重要,有了同伴便可以忍受。大家茫茫然走著,施先生茫茫然走著,那人剛剛不見了。那人的身體瓦解了。一片片皮肉掉盡,身體剩下沉重的骨頭,無法支撐繼續走動,半途散落於地上。還記得那尋覓焦點的瞳仁,眼球滾落的一刻依尋覓,遭行人一腳踏碎了。人數正續步減少,沿途不少人如那人的樣子,身體瓦解了,捱不住到未知的終點。一堆堆紫黑色的頹喪人體殘骸,像一座座隨意立下的墳,草率把屍體埋掉的結果。沒有碑,沒有十字架,更加沒有死者的名字。
不知道過了多久,所有人都倒下了,四野剩下他一人,身後盡是人體殘骸墳堆。彷彿意識到他們要走的方向,他信步前行。遠方是連綿山巒,亦略帶紫黑色,大大小小一個挨著一個的巨人墳墓。他心想就是那邊。
行走,風景在流轉,流轉,逃不出荒天荒地。天地景色似是在他身邊跑過,而他根本沒有移動,因為走了些時,他依然沒有走遠那些殘骸墳堆,山還是那麼遙遠。簡直是個騙局。他已經筋疲力竭,絕望的頹然跌坐地上,不願意動,無可奈何的望向橙紅天空,血海的水流流到遠方。
為甚麼要走?到底哪裏是哪裏?他開始懷疑跟隨他們走是錯誤的。自己根本不想走。然而,如果不跟他們走,他留在原地,他又會如何呢?沒有人能逃過死亡,他們一個一個死去了,他也不例外。他抬不起手,可能在中途掉落了吧。
鼓聲再次響起,像預告甚麼。
遠山天邊很紅,紅得滴血,何時聚集了黑雲,形成巨大漩渦,遮住天空,慢慢迫近。他等待末日,不理它是雲是風,靜看這一切。甚麼掉落施先生的鼻子上,他鬥著眼睛,一雙火紅網眼,兩觸鬚似角,嘴巴如機械組件裝嵌而成的生物。施先生有點慌張,那生物亦然,一下子飛走了。
這種情況,施先生曾經在自然紀錄片中見過。突然而起的黑雲,嚓啦嚓啦降下數千萬隻蝗蟲,蝗蟲所到之處不論是農作物或雜草,三四天內全被吃精光。農民遇到這情況,無地往空中一抓手,讓拍攝人員看,是四五隻。他們噴殺蟲劑,蝗蟲死了一批又來一批補上,以某種形式復活過來一樣。於是農民只能夠眼白白看著農作物被吃精,聽牠們機械組件一般的嘴巴磣磣運作,迅速蠶食世界。
外國科學家曾經研究蝗蟲現象,嘗試尋找防止蝗蟲這自然災害出現的方法。他們在實驗室飼養蝗蟲的原形—草蜢。經過長時間的觀察,科學家發現草蜢是不會對環境造成災害的,造成災害的是牠們變成蝗蟲之後的事。草蜢不會不斷吃東西,只吃所需要的便停了。當草蜢數量增多,牠們感覺到自身環境的擠擁,便開始感到不安,覺得有競爭的必要。一有了這種意識,牠們就進入蛻變階段,脫去原本青綠和平顏色的外殼,換上一身戰鬥格調的墨綠色,變成了蝗蟲。儘管蝗蟲的生存條件並不比草蜢所需的要多,但牠們一經蛻變便陷入不安的情緒中,急地吞噬超過生存所需的一切,彷彿只有吃掉世界才能得到安慰,任憑情緒驅使,毫無意義的一直吃一直拉,飛到哪裏吃光哪裏。
施先生此刻亦聽著那機械組件嘴巴在攪碎世界的聲音。蝗蟲湧向他,籠罩他,然後飛向他身後一座座人體殘骸墳堆,停伏之上,不久,成為一堆堆密密麻麻湧湧移動的蝗蟲群體。牠們往人體殘骸墳堆裏鑽,啃吃紫黑爛肉,直吃見其心臟,唯心臟依然鮮紅,牠們便全放棄肉,轉伏其上,滋滋聲,不消多久,吃掉一個。又一個心臟被吃掉,一個接著一個,牠們都意猶未盡,吃完一個心臟便一整群體的移往尋覓另一個,團團烏雲升起又降下。不知道牠們到底吃掉了多少個心臟,血肉淋漓的場面,施先生看呆了,突然發現身上也滿佈蝗蟲。一隻猛鑽向他的胸腔,鑽出個血洞那刻,他感到幾乎透不過氣來。小東西進入他的體內亂竄,其他的紛紛也鑽進牠率先鑽開的入口。胸口鮮如注,不知覺間,施先生看見自己的心臟被瘋狂啃吃的景象。
夢三。
路被霧迷白,他僅見咫尺之內朱紅的鋪磚,優雅地砌出織紋圖案,那種像是歐美國家市區才有的街道,充滿繁華的贅重感。完全感覺不了寒冷,施先生卻認為那是十二月冬季的時節,於是他伸出手時,手上正戴著孩童時母親給他做的棕色毛線手套,一次因為與父親玩耍,他跌倒在地上,左手的那隻手套掌心破了個小洞。母親後補好了。那小洞現在還在。長及大腿的厚絨大褸翻著飄雪,黑色圍巾上也積著霜,像反光的絲絨。他要探望移民到了美國的兒子。前妻嫁了美國人,那美國人頂著大肚,一雙蔚藍眼睛,兒子以英文叫那人做爸爸,體型已經一模一樣了。他們天天吃漢堡包薯條汽水。他買了一份禮物送給兒子,想跟前妻商量,讓兒子跟他回香港一下,看看失去了眼珠和失去了一隻腳的嫲嫲。店員把禮物包成一大份,閃亮的花紙,又紅又綠,甚有聖誕氣氛。內裏是甚麼,他忘記了。
這條路能引領他到前妻的住處,他十分相信。突然間前面迎面而來一個小孩,身材矮矮小小,往他直跑。他只見小孩剪成椰殼頭的頂,小孩一直低著頭。眼見小孩要撞過來了,施先生躲開一邊去,小孩跟隨著他躲去的方向轉移,就像是特意的,小孩猛然撞到施先生身上去,然後繼續跑往不知名的地方。施先生回看那漸漸離去的矮小身影,想不到小身影的主人也回望,是個非常漂亮的小男孩。施先生沒有辦法形容那小男孩有多漂亮,因為根本連小男孩的眼耳口鼻也沒有看清楚。但是,總之非常漂亮。
施先生回過頭來,又走著自己的路。霧裏所見,景象漸催黑暗,朱紅鋪磚也染上了深藍,天是要快黑了。施先生加快腳步。這時候,又一小孩迎面跑來,這次是一個小女孩,穿著小巧粉紅色花邊裙子,他只見小女孩扎著孖辮分成兩邊的頭頂。小女孩也向他衝過來,他又作躲避。可是,小女孩就如剛才那小男孩的化身,也跟著他轉移的方向移動,最後直撞到他的身上去,又默然離去。他看她,他也回頭看他,又是一個漂亮的孩子。
他想著,這到底是否孩童間興起的惡作劇方式,兒子是否也參與過這種遊戲。
不得了的,幾乎看不見路,黑夜真的要來臨,於是施先生不再想下去了。然而,面前又走來了一個小孩,跑過來,撞到施先生身上去。施先生來不及反應,又一個小孩跑向施先生,向施先生撞去,一個接著一個……
施先生想知道他們要往哪裏去,追隨他們的身影走,未幾,便見黑暗中亮著日光燈的店舖。店舖位於黑暗的角落,就只有它。店舖門前擺放著旋轉彩色滾筒,緩緩自轉向上扭的彩帶,紅白藍,無窮無盡。孩子們魚貫走進店舖裏,也是 無窮無盡的。施先生站於店舖門前張望內裏究竟。
從店舖門口看來,理髮店小小的,玻璃推門和一小段玻璃牆已是理髮店外觀裝潢的全部,連招牌也沒有。可是看進店舖內部,便發現店內的空間一直深長入去擴展,見不到盡頭,兩排理髮專用椅子一直排入去,椅子上都坐著了小孩,孩子走進去總是還有座位。
理髮專用椅子擁有牙醫病人座椅的外形,椅背和座位皆可以調校角度,腳踏位可推開來收進去,可奇怪的,椅背後支出個像電髮器的環形白光燈,一隻白色的洗滌盆橫置於座位上人的前面,使孩子們像是坐在囚禁嬰兒的連體桌椅。施先生再看清楚那些正襟危坐的孩子,原來雙手雙腳也綁上了皮帶。每位小孩在椅子上都動彈不得,但是他們看來也是沒有要動的意思。他們漂亮得難以言喻的臉被頭上的燈光淋得絕白,影的絕黑,有點森森然的可怖。
施先生無端的焦慮起來,不知道如何是好,說不出是甚麼感覺。
孩子們面前也有一面長鏡子,鏡子照不見人,似是風吹弄水面,盪著漾漾水光。在孩子坐下之前,理髮師早已站在椅子的後面,他們為孩子調校椅子的角度,高度,然後綁皮帶,雙手,雙腳,一而再,再而三的檢查皮帶是否綁得牢固,拉得緊緊的,肌肉在皮帶的兩邊鼓起,幾乎是透過皮肉綁死孩子的骨頭。雖然如此,孩子的臉上沒有痛苦的表情。
理髮師都穿著白袍,下面是黑色西裝長褲,除卻髮型臉型和身型,外貌都幾乎一模一樣,似城中某位成功人士。那位成功人士最近得到了世界最傑出經濟人獎,報章雜誌紛紛訪問他。施先生見他常出現於電視節目接受訪問,那個油汪汪的光頭像鎢絲燈泡一般,總叫施先生不期然地撫摸自己依然濃密的頭髮,而且眼睛有被照得暈眩刺痛的感覺,不單是施先生如此,連最專業的訪問員也頻頻低頭看稿。
「成功之道是—」世界最傑出經濟人獎得主笑起來了。
施先生曾經在書店閒逛,翻過一本相學書。富貴之人的面相皆怪異,這就是施先生看過那書後得出的結論。富貴之人面相的特徵:寬大額頭,巨大鼻子,厚嘴唇,細長眼睛,圓頭圓身圓手圓腳圓指頭。那位成功人士也有上述大多數特徵。寬大額頭無邊無際是最明顯不過的,厚大嘴唇和圓的身材法則也十分特出,配上大而無當的豬膽鼻,既圓又小的鼹鼠眼睛,也真夠怪異了。
只要你見過那成功人士的笑臉,便很難忘記。光滑額頭泛起漣漪般的波浪紋,兩道短促的眉毛往太陽穴下滑,眼睛細圓而凸,在眼鏡背後努力擠成笑縫,巨大鼻子又稍微脹大,嘴巴向上彎向兩邊擴展。電影台還為那成功人士製作了特輯,在介紹他的家庭背景時,有他的全家合照。他的祖父祖母,父親母親,兄弟姊妹,五官尋常,不突出,與常人無異。這不禁令人產生疑問:到底那張嘴臉是遺傳自誰的呢?
那成功人士的笑臉真的像是雜技團表演的軟骨功,能人所不能。他臉相的奇特與他的大嘴巴有很大關係,因為實在非常特出,以致人人看他的第一眼,目光自然停留於其上。他的嘴巴閉著時也是常人嘴巴大小的兩倍,而笑的時候更是張力驚人。兩顴肌肉向上牽動,嘴巴往兩腮彎和伸展,到某處便應該停下來了,但視覺上的錯覺看來仍在伸展,超過臉腮,超過耳朵似的。以為他發出的是豪邁笑聲,可卻是從胸腔吐出透過齒縫拼發出的陰冷聲音。
現在理髮師亦裂著無限大的嘴巴,睜著精神亢奮的圓眼睛。理髮師在腰間拿出兩個小小圓球,像是乒乓球,不過要小一些,把它們放到一旁的小桌上,滾動了一陣子。理髮師又從長褲口袋掏出一支金色茶匙,搖晃光下,似要查明真偽。確定無誤,理髮師蒼白的手扶著小孩的頭。小孩不作一聲乖順任由擺佈,頭被扶到哪個角度便靜止在哪個角度,彷彿頭的主人不是自己。
理髮師湊近看小孩的臉,直視小孩的眼睛,表情冰冷,執著金色茶匙利落地插入小孩的眼窩裏。小孩似乎顫抖了一下,又似乎沒有,定定的睜著眼睛看著執著金茶匙的手轉動,攪動,轉動,攪動。一拔出金茶匙,小孩的眼球隨即彈出,掉落到洗滌盆裏。一股血湧出空洞的眼窩,但立即止住了。理髮師熟手地把小圓球放進小孩的眼窩裏,小孩的眼皮立刻變小變緊,變成了天衣無縫的鼹鼠眼。
孩子的雙眼都被換掉了。施先生身邊開始聚集了很多人,他們都看全了整個血腥過程。
理髮師扭開水龍頭,水急流出,洗滌盆漲起水,小孩的眼球浮起,水成旋轉狀,成為旋渦,眼互相碰撞,血水下降,流盡,眼球先後掉進排水口。孩子挾縫著新小眼睛,漠然又好奇的看那消失的一切,眼球被挖出時流出的血液凝固於臉上,像掛著兩行血淚。
伸手托起小孩的臉,理髮師審視改造的效果,滿意的點頭。接著,他亮出一把剃刀。先以剃刀輕刮去孩子臉上的血淚,把沾上血的剃刀往衣袖上抹淨﹔刀落下皮膚裏毫不費勁,孩子皮膚如濕潤的陶泥,切割位置的皮膚微微濃起亦像是陶泥被切割的效果。血液一絲絲一絲絲滲出,傷口乍現出白膩脂肪。剃刀移轉,孩子的臉便向那邊牽動,臉容隨剃刀的游移而扭曲。孩子的嘴巴變成無限擴展的裂縫。孩子簡直像是一個小成功人士了。
一鬆綁,孩子們一湧而出,跑過來衝往施先生周圍的人的懷抱裏,擁著那些人。那些人端詳孩子的新臉。孩子們的樣貌都差不多一體化了,而且未癒合的傷口鮮血淋漓,十分可怕,又是那成功人士醜陋無比的臉孔。施先生以為他們會粗魯地把孩子推開,但是他們不單把孩子擁抱得更緊,竟以贊賞的目光對著孩子微笑點頭,眼角流出欣喜滿意的淚水。
這天施先生又從噩夢中醒來。再不能入睡,他坐在窗前的安樂椅上等待天亮。在他半躺著的位置,看到天空的一小角,重重樓宇間的一個破洞,破洞由黑暗變幻了多少次顏色,全亮的天是灰黃濛濛的,煙霞纏繞香港的日子。如果有人問施先生覺得香港是如何的,施先生會把此刻所見的告訴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