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註冊,結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讓你輕鬆玩轉社區。
您需要 登錄 才可以下載或查看,沒有帳號?註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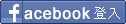
x
本帖最後由 derek1106 於 2014-3-1 10:21 編輯

目明
1 他早已習慣,眼中那些縈繞不走,朦朧而又不能忽略的光點。
那叫飛蚊症,醫生說。這不影響健康,他也懶得去理。雖然在陽光下,那些無以名之的小點會令他有種暈眩的感覺,就似,就似離地而行的感覺。他用盡詞彙也只想到這樣的形容。但在這個沉悶、黑暗的停車場中,細小的看更亭內,就只有這些小點和他,又有什麼所謂?況且在這樣的環境下,他覺得,這些眼中揮之不散的積聚物,有種莫名的親近。
無聊的看著時鐘內秒針的運行,「滴嗒」一圈如往常般慢。那所謂十小時的工作看似沉重,其實真的不算太累。他就只是在那個看更亭中坐著,至於開關閘門這些事,早已轉成自動化操作。他就只是可有可無的坐著,途中進行三次巡邏,又回到那個亭中,坐著。
直到接更的陳伯來到,他才可回家,天上泛起魚肚的白,他從來沒見過如電視電影中,天空中有一抹火燒的紅,一次也沒見過。白,天空就只有白。街上只有要早起工作的路人,又或,尚未可休眠的歸人。
「雪櫃有湯,叮熱可喝。」桌子上的字條和床上的樺。他把雪櫃打開,有湯,還有飯菜。他放進微波爐,微波爐透過玻璃,亮起朦朧的橙光。眼內的小點在橙黃的光下,顯得有點不確定。越想捕捉,越是難以尋到。他就這樣在微波爐前楞楞地出神,不知不覺地睡著了。
直至微波爐刺耳的提示音響起,他才驚醒過來。他搞不清自己到底是睡了一個短促的覺還是發了一個漫長的呆。沉重的頭顱卻因那「叮」的一聲變得清醒,他看著微波爐中湯面浮起的圓形的油份,他有種自己就在那一個個圓之中的錯覺,而樺,又在哪一個圓呢?
他沒有喝那些湯,就只是把飯菜吃光,沒有言語,就只是看著樺的背。漸漸變亮的天空,光線照進房內,樺的背。他沉默,把湯倒掉,躡手躡腳的上床。不一會兒,他又下床,在字條上補了一句。再回床上,這次,他久久沒有起來,應該,是睡了。
「湯有點咸,下次放少點鹽。」
醒來後,他總是在回味睡夢中的故事,是的,他已經很久沒試過一寢無夢了,自從他少年時期。他發了很多很多個夢,夢中的故事從來都不一樣—或是前塵往事,或是如光泡影。當然,在某些夜晚,是綺妮纏綿的。
他習慣在床上回想一下,夢中的故事的意義。為此,他還上過一個解夢的課程。雖然最後也得不出什麼答案,但往往只是回想夢中的吉光片羽,他也有種滿足的感覺。
這種習慣就似在沒有天敵的空間長大的物種,不知覺間已經變得龐然巨大,他有點害怕面對這種未明的物體。他不是沒有驚懼,但伴隨恐怖而來的,是對這種未知的想像的依戀。他就似一個吸毒的癮君子,不知在何時開始,他醒來後,就會這樣躺在床上,直到,新的一天開始。
桌子上有一條寫著「嗯,我先走了」的字條,他隨手拋進垃圾筒。夕陽昏淡的光照進屋內,有些沉重,而且飄著油溢的香氣—鄰家那個煮飯用油極多的伯伯,已經準備晚飯了,和老伴一起。他也在準備。
新的一天,來臨了。
陳伯把停車場的鎖匙交給他,順便提醒他,老闆說今晚有架大貨車會泊進來。陳伯說,留意一下,貨車來了,把閘門都打開,方便人家。
「怎麼這個地方都有大貨車,看來有點邪門。」陳伯說。他知道,所謂「邪門」,與鬼神無關,只是這個城市的陰暗面,沒什麼,他早已習慣。
這遠離市區的停車場,已經很久沒有貨車停泊了。他還記得,每當有大貨車經過門閘,這個在旁的看更亭總會一陣震動。放在桌上的水杯中的漣漪在說著震動的幅度,和外面卡車的大小。他眼中的小點也彷彿跟住震動搖擺,有一種搖晃的感覺。
他曾經以為,這種搖晃是一種絕望,但直至不停成長,身軀由細小瘦弱變得強壯碩大,生命依舊擺動不定。他開始相信,這是一種平常的節奏,而且,如人與神之對話:定必直到永遠。
剎那間,他彷彿看到一抹青色的閃光。母親對他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
2 母親唱兒歌的樣子,他永遠忘不了,他認為那是他生命中,最驚悚的一個畫面。 他印象中,母親總愛扎一個巨大得不便工作的髻,就似戴了一頂烏黑而奇怪的帽一樣。父親在他還未懂事的時候,已然逝去,或許因為如此,他從沒有看見過母親的笑容。她瘦弱、蒼白,就似每一個童話故事中的女巫,他曾經信以為真,並害怕有一天,母親會因飢餓,而將其吞食、咀嚼,以那一排潔白的牙齒。
直至有一天,他看見母親把一個強壯,有點不修邊幅的男人帶回家。母親叫他向人家打招呼,他只是楞楞地在看著那個男:他看過父親的樣子,在照片中。高高瘦瘦的,帶一副如女性般纖細的金絲眼鏡,穿一身西服,高瘦的身材顯得挺好看的。
這個男人,穿著一件普通的襯衣,一條牛仔短褲,露出厚厚的腳毛,進門後,大力的揉了他的頭一下,笑了笑。媽對他說:「叫人啦,叫叔叔。」他從來沒聽過,母親如此溫柔的叫喊。
飯後,母親把他哄上那張,細小的雙層床睡覺,他看著母親和那個男人離開房間,他曾經想過,把母親留下,但看見那一排潔白的牙齒,他不敢提出任何要求。關燈後開門的一瞬間,就似火車穿過隧道前看到的光亮,他覺得自己是火車的最後一列,而且列車掛鉤已經脫落。門漸漸關上,無邊黑暗再次包圍,他不由打了一個顫。
其後,惡夢叢生。
他發了許多惡夢,他夢見自己作艷麗蝴蝶,被困於無邊蛛網,千辛萬苦擺脫後,又於平靜湖面上驚覺自己只是飛蚊,蛛網只是電蚊拍,在一瞬之後,電成白灰,燃燒殆盡。他就驚醒過來。又夢,他夢見自己摔成三千塊碎片,不知為何,他就清楚是三千塊,支離破碎的痛感令他不能思考,只能看見有人把石頭從每一塊碎片輾過,成為碎粉,那人有一個巨大的髻,高瘦,穿一身西裝。
他再夢,在一條平緩水暖的河,漫天的星光,船輕輕的搖曳。那是一種如蟲在噬咬床舖的晃動,有兩個赤白的光源。光源互相糾纏,攻伐,他隱約看到其中一個光源化成母親的模樣,表情扭曲,又看見另一個光源化成那個男人,不一會兒又變作父親。他嗅到腥臊的氣味。光源漸漸停戰,他認為,是其中一個,把另一個,完全吞沒。
他醒了,看見母親在床邊看著他,上層床的高度令他只看見幽幽的兩隻眼,發出赤白的冷酷的光,就似狼的眼。母親似不知道他未睡,依舊哼唱搖籃曲:「搖啊搖,搖到外婆橋。」
他偷瞄下層的床,看見鼓鼓的一個人形,卻看不過任何實體,就似一個黯啞卻貪婪的黑洞。
那夜過後,他的眼睛開始有小小的光點。或許是那戰敗的光源,在他眼中,留下破碎的痕跡。他開始每晚失眠,漸漸變得夜不能寐。
而倘若能睡,那一覺,必然大夢臨頭。
3 刺耳的響號聲如野獸的獰笑聲,充斥了整個空間。他驚覺一輛殘舊的貨車在閘外,車上的司機咬著煙,心中的不耐煩由不斷拍打的響號和口中噴吐而出的粗言穢語表達出來。
他默默的按下開關,把閘打開,車上的司機卻沒有放過他,依舊吵吵鬧鬧的。「你係唔係做野架?咁慢手腳?我秒秒鐘幾百萬上落架!你老母!」他皺皺眉頭,想起自己以前。他曾經每晚在雙層床上上落落而不能睡熟,他不明白,上落,又有什麼大不了?
車靜靜的開進停車場,兩盞車尾燈就似兩隻陰森的眼睛,在黑暗中偷窺著他。就似母親、樺,甚或陳伯的眼睛。
每個人的眼睛在他的腦海中,都帶著赤白的,幽幽的光。似是深鬱森林中,一隻隻飢渴的狼。
他是看過狼的,在內地的動物園,和樺一起。自他生理時鐘失調後,他就只能放棄學業。生活逼使他找工作,通宵營業的便利店、凌晨清潔街道的清潔工、專做夜宵生意的大排檔……這個城市的晚上的工作,他通通做過。
在這之前,他從沒想過,這城市的夜是那樣的豐盛,只要你想,總能夠生存。又或者,他已分不清日夜的界線。醫生說,那些光點並無大害,但他卻覺得,眼中的光點越來越明顯,就似一個個閃爍的光體,只要有較亮的燈光的地方,就會發出刺眼如日的光芒,只有在絕對的黑暗的地方,他才有喘息的機會。然而,這似乎對他沒什麼影響—一個本來就依賴夜晚的人,又怎會介意,日光的傷害?
直至他在中港運輸的工作,發生意外,在內地的醫院裡,遇到了樺。
樺當時穿一身純白的護士服,她拿著手上的病歷,問:「你是香港人?」他點頭。就這樣,他們約會了,荒唐而不可笑。
樺的工作,是沒什麼時間概念的。有人需要,她就要去,她是這樣對他說。但只要願意,總能約會的。樺和他去了動物園,當然,是夜間動物園,主打尋幽探秘的那種。
他就在那裡,看見狼的眼睛。幽幽的,赤白的,一眨一眨,在黑夜中,竟似是一顆顆星星。樺在旁緊緊捉住他的手,合適地表現一個女性應有的表現。「怕。」她說。他沒有趁機會抱緊樺,沒有上演那些俗氣的電視劇上的情節。
他只是幽幽的,赤白的,看著樺。樺全身的疙瘩都浮起來了,她有種自己成了獵物的錯覺。
突然,觀光車剎車了。劇烈的震動制止了兩人的互望。他與樺都像球一樣滾到草地上。導遊說,觀光車引擎壞了,要等另一架觀光車來接,在這個群狼環顧的地方。導遊似是開玩笑的說。
這大概是生命偶然的震動,造成了他們之後的婚。那一刻,樺捉緊他的手,緊緊的,說:「不如,婚吧?」他沉默了一會,點了點頭。沒人知道,在震動之後,他眼中的光點變得紊亂,他只是在無意識的,搖動自己的頭顱。
但既然如此巧合,他也沒所謂,那就婚好了。
婚得如此倉卒,準備自然不足。幸好,他的父母已經去逝,樺的父母也是老實人,沒怎麼刁難這兩口子,就這樣平凡的婚,請兩三個老朋友和親戚,在大陸辦的婚禮。最麻煩是請假,醫院近期死的人、病的人有點多。樺是這樣形容的。他聽著,有種自己也不過是死的、病的其中一個,不過碰巧樺較用心照顧的感覺。
婚的一夜,樺是三月撥扇,滿面春風的。就似一隻蝴蝶,穿著租回來的,紅得如一個爛熟的蕃茄的裙褂,滿場穿插。他只是坐在酒杯前,看著眼中的小點在酒精的揮發下,變得更為迷糊。直至喜宴完結,他方發現:噢,原來已經完結了。
那夜他第一次看見樺的裸體,在深紅的裙褂下。酒精影響之下,他和樺就這樣做起愛來。他不斷擺動身體,眼內的小光點如悠悠球般上下不定。不一會兒,一下青白色的閃光在他眼中,如閃電轉瞬即逝:噢,原來已經完結了。
4. 婚後一切塵埃落定。樺申請了來港定居,幾經輾轉,又做回了護士。他也換了一份停車場看更的工作。畢竟兩夫婦都在香港,生活也過得舒心一點。樺是這樣說的。他無可無不可,也就順順樺的意思。
樺來了香港之後,和他各有各忙,偶爾放假,也各有節目,這在旁人眼中,竟是夫婦和順。這倒也對得起他們請柬上的那四隻金漆大字:可喜可賀。
但他這漫無目的,只有眼中小光點伴隨,巡邏生涯畢竟是開始了。
在這暗啞沉默的空間內,如鬼魂般徘徊。看著一隻隻老鼠在角落裡繁衍,各種昆蟲的屍體在無人所曉之處堆積,看見生命不斷消逝又誕生……似是被咀咒的地縛靈,只有越發頻繁的青光在提示他—正在衰弱,乃至老死。
5. 貨物上落的聲音在空曠而安靜的空間盪鞦韆般不斷變大,是時間去巡邏了,在這熟悉的地方。
穿過一輛輛車排成的迷宮,他習慣這地方的不變,直至看到那輛與別不同的大貨車。貨車霸佔了兩個泊車位,那個司機和幾個工人,把一個個木箱從車尾處搬出來,他看不到箱中有什麼,只是奇怪怎會在這裡作運貨的中途站:這裡實在有點偏僻。
他有意瞟了一眼,就無故惹來了事端。「望咩望啊,死保安仔!」司機對他咆哮起來。他沒打算理會,只是那名脾氣明顯有點衝動的司機竟擋住他的去路。
「死保安仔,識唔識應人啊?你啞架?出句聲啦!」他想了想,還是沒有回應,他側側身,打算避過司機。司機自是如一般電視戲的反應—把身子擋在他前進的方向。
他忽然發現,自己有點難以應對這種場面。他已忘了多久,有這種手足無措的感覺。「你究竟想怎樣,說一句話啊!」樺抓住他的衣袖,不斷的搖動,彷彿他已經昏迷一樣。
樺身穿一套孕婦的衣裝,脹大的肚子和瘦弱的身軀不成正比,他看著樺,有種無能為力,疲累的感覺。又有誰能夠知道,樺渴望的孕,會是如此結局?
而更荒謬的是,他覺得,那鼓起的肚子內,不只孕育著孩子,還藏住一些其他東西,他不知道是什麼,但就是覺得,有些其他東西。
「孩子有你的一份,要還是不要,你都要說一下啊!」樺的聲線越來越沉,大概是用盡氣力了。他想。到底該怎樣,他也不知道,難得而來的孩子,患上難得而來的疾病。一切難得,自然,難失,他明白樺的想法。
不如放棄孩子,不幸中誕生,只會誕下另一個更大的不幸,他想。但他又知道,樺對孩子的渴望,又或說,是從他身上,轉移過去的希望。
他看著樺,正想說什麼,眼中的青光一閃,便只能閉上眼去。睜開眼後,他看見樺的雙手下垂,乾涸得就似枯萎的樹枝。樺閉起的雙眼卻令他感到一陣輕鬆,他為此感到一陣的羞愧。
五個月後,樺還是誕下了孩子,他看著孩子細小,如臂般的大小的身軀,那微弱的起伏的呼吸,他有種想哭的感動。數日後,孩子始終因病死去,在他和樺的四臂包圍之中。
他母親是在醫院中纏綿了半年,才死去的。他一直以為死亡和生存一樣,是一件無比困難,就似在棘路上行走的旅程。直到孩子死去時,他方發現,生命的離去是這麼容易。感受著手中那漸漸冷掉的體溫,看到樺滿臉的淚痕,他腦海出現了一種想法,而且,如芒刺背。
孩子的死,或是生命中最大的幸福,無論是孩子,還是他。他們都逃過了最大的不幸。每當如此想,他是悚然一驚。他覺得,就連自己眼中的光點也變得猙獰起來。
那個司機把他推倒在地,狠狠地撞到那些搬運中的木箱上,他感受到背上傳來火辣的痛楚,濕潤的感覺從衣服中傳來,他流血了。在劇烈的運動下,他眼中的小點也開始不規則的運動起來,就似微波爐中加熱的湯,不斷的顫抖,那些小點就似一個個氣泡,在眼中膨脹爆破,他想說話,卻只可發出無意義的呻吟,眼中不停流出淚水,在水光之中,他看到一個青色的小孩的模樣。
他看到他。
6. 孩子的喪禮很隆重,樺說,小傢伙生出來沒福氣,死也要死得有福相。西式的喪禮比較溫柔,孩子應該較喜歡,樺又說。他不置可否,也沒有置可否的權利—他覺得自那日起,樺已經不太理會他的回應。
但奇怪的是,樺不是無視他,她會買衣服給他,而且定必稱身;會煮飯,而且都是一些那怕用微波爐加熱多少次也可口的菜式;他不用擔心房子的問題,那怕廁紙還是剃鬚刀,都一定安得其所。而且,有什麼重要的事情,樺都一定會和他商量,就像這次的喪禮,但他總有種不由自主的感覺,到底是他沒有主見,還是樺沒有理會他的回應?他不清楚,但稍稍偏向後者。樺會和他說話,但卻只是單純的說話,沒有其他什麼存在的餘地。就似每個女生成長時的那個娃娃,他這樣想過。
於是,喪禮就如此進行,訂教堂,制棺,辦死亡證,甚至派帖。他感到似曾相識,樺在婚禮之時,也是如此吧?兩者驚人的相似,他在心中默想,如果可以,他想笑出來,在喪禮之上,孩子的屍體就在前方,他知道,不可以。
當神父要其他人逐個上前瞻仰遺容時。他發現,在其他人的對比下,原來孩子的屍體是如此細小。小小的床棺恰好可以容納孩子的身體,如果孩子還生存,大概已經不適合用這棺槨吧?畢竟聽說小孩成長的速度很快的。又如果有靈魂……對了,如果有靈魂,孩子的靈魂會長大嗎?他無意識向前踏一步,就似想看清什麼似的。
他的眼前,是孩子的屍體,紫紅的屍斑隔著小小的床棺依舊清晰可見。四周是天使和教堂的繡錦,天堂是這個樣子嗎?他抬頭望望教堂,光芒從不同角度的玻璃透進來,有種神聖的感覺,高而空曠的天花中畫滿天使。他流起眼淚來,光點在淚水模糊了的眼中越發明顯,他聽到天使的歌聲,充滿回音,他知道,是教堂在播錄音帶。
其後,他就暈倒,在滿目瘡痍的青光下,在昏迷之前,他知道,其他人會誤會他是傷心過度,只是他知道,這或許是上帝對他的懲罰,因為他在孩子的屍體前,雙手第一次互相交纏,他大概記得,祈禱是這樣的手勢。
但願天堂不是如此模樣,他第一次如此渴求一件事情。
7. 他醒來後,樺抱著他,陳伯在旁:「你就這樣暈在地上,嚇死我們。」陳伯說,發現他時,就只有他一個在停車場中,緊急視網膜剝離,手術順利完成,但他的視力已經大幅減退。
陳伯走前留下了兩個橙,和一封利是。他說,是公司上頭給的。他們說,那晚什麼都沒有發生過,陳伯嘆了口氣,把利是塞到他的手上。你還要生活,好好生活,陳伯說完就一顛一簸的離去。他看著陳伯的背影,覺得有點難過,他不知道這種感覺從何而來。
「幸好送院及時,否則就有生命危險。你說,如果你有個什麼萬一,叫我一個人怎麼過呢?」樺扶著他離開醫院時,陽光絢爛,他眼中已沒有那些小點,只有一片如磨沙玻璃的模糊。他覺得,好似有什麼改變了。
他第一次感到安定的感覺,他覺得,雖然要失去一些視力,但終於可以擺脫那滿目小光點帶來的搖晃感,還是值得的。
直至回家路上的一個踉蹌,他整個人失去平衡。
剎那間,那種熟悉而陌生的失重感覺又回來,而他知道,這將如人之衰老:定必伴其一生。
|